【学术观点】郑熙青:学术粉丝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自粉丝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挑战
摘 要:当今英文学术圈中的粉丝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粉丝文化研究自下而上关注民众如何接受和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研究者的“学术粉丝”(aca-fan)身份指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方式和样态,它承认研究者可以既是粉丝社群中全情投入的爱好者,也同时能是熟悉文学和文化理论,可以对粉丝社群的现象和文本进行有效分析的学者。由此,有关粉丝文化的研究就成为一种研究者对自己所处的人群的自我民族志,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身份代表和伦理的争论。文章总结梳理英语粉丝文化研究中关于“学术粉丝”的相关讨论,并指出这种混杂身份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可能使用方式和场合。
关键词:学术粉丝;民族志;研究伦理
粉丝文化研究在中文学术圈还是一个非常前沿且边缘化的领域,但在世界范围内,这个领域已经有30年左右的历史了。真正将粉丝文化研究单独作为一个领域从更大范围的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判中区分出来的,主要是粉丝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明显区别于前人的视角、态度和研究方式。当今英文学术圈中的粉丝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因为粉丝文化多种多样,涵盖的媒介平台和形式过于广泛,而判断是否“粉丝”的标准又非常模糊,所以很难用穷举和大数据的方式严格统计和归纳,这时更多需要的是个体化、细节化的观察、研究和论述。同时,依赖民族志等基于个人视角的观察方式,也是因为粉丝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在情感上的文化,需要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说清其中关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e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ck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主要都以从上而下的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他们从文化产业的产品出发,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控制[1]。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著作开始,研究者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以及普通民众。流行文化研究渐渐地出现了研究民众如何接受和使用文化工业产品这一角度,自下而上地观察社会和文化。英语世界粉丝文化研究的脉络正是从这里开始,看普通观众如何在接受和批判中创造性地理解和重塑文化工业中的大众文化产品,并显示和赞扬普通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这样的理论和视角首先就发生在一些建立在民族志观察基础上的研究中。粉丝文化研究者中最早一批的代表性学者,如卡密尔·培根-史密斯(Camille Bacon-Smith)、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康斯坦斯·彭利(Constance Penley)、约翰·图洛克(John Tulloch)等等,都多少参与过粉丝的文化活动,在讨论粉丝文化时以灵活多变的方式加入了自己的经验和普通粉丝的观察和意见。这些内容有些是以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方式加入讨论的,例如培根-史密斯在《进取的女人们》中细致描述了自己加入美国电视剧《星际迷航》粉丝社群的全过程,有些是以采访和数据统计描述进入的,例如约翰·图洛克对英国电视剧《神秘博士》粉丝的量化分析,还有一些是将在粉丝社群中获得的经验和信息糅合在文艺理论和文本分析中呈现出来的,例如亨利·詹金斯和康斯坦斯·彭利的著作。不同于文化批评的远距离和学术圈惯常的“中立”态度,粉丝文化学者一方面会明显地表露出对所爱之物的热烈喜爱之情,并显示自己身处社群之中,为社群代言的身份;另一方面,他们仍然熟练使用学术界的理论和分析话语,呈现出跨界的身份和研究视角。这一身份和写作模式由亨利·詹金斯开创,在日后被同行学者概括为Aca-fan(我在《文本盗猎者》书中的翻译是“学术粉丝”,也有翻译成“学者粉”的),指的就是这种混杂着学者和粉丝身份和立场的特殊研究视角。
本文将简单地介绍英语世界中粉丝文化研究领域的简单历史和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学术粉丝”的由来,着重点明“学术粉丝”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在该领域中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反思这种分散的个人化立场和研究作品的缺陷,并提出中国学者需要做出的贡献和回应。
一、英语粉丝文化研究的三代研究者和研究立场
在粉丝文化研究理论出现之前,学术界和大众传媒领域对粉丝文化都有一些固定的污名化刻板印象,例如看到自己的偶像就尖叫晕倒的女性粉丝,痴迷某个明星所以因爱生恨发生暴力行为的男性粉丝。一些极端的个案,例如美国因爱生恨枪杀约翰·列侬的大卫-马克·查普曼,或者企图靠刺杀里根总统获得自己的偶像朱迪·福斯特注意的约翰·欣克利等等,都进一步地强化并加剧了西方社会对“粉丝”这一身份和群体的偏见。其他较为温和但同样负面的刻板印象,还包括例如无能的心智如幼童的成人、无法将虚构故事和真实世界区分开来的妄想者等等形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粉丝文化研究起步的时候,这样的刻板印象是西方世界媒体中最常规的,粉丝在这种语境中呈现出一种文化蠢货的形象。
在《粉丝圈:媒介化世界的身份和社群》一书的前言中,编者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康奈尔·桑德沃思(Cornel Sandvoss)和C·李·哈灵顿(C. Lee Harrington)将粉丝文化研究这个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至该书出版的2007年之间的粉丝研究学者粗略地分成三代[2]。他们指出,第一代研究者的主要研究灵感来自法国文化研究学者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的文化理论,着重区分了权力者拥有的大规模的“战略”和无权力者即时的因地制宜的“战术”[3]。粉丝文化研究因为这种立场获得了代表无权力边缘人群发声的合法性,这种边缘性按照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说法,是“受宰制社会形构人群的文化品位,尤其是因为性别、年龄、阶级和种族的组合中丧失权力的人” [4]。在这种意义下,这一代粉丝文化研究学者的写作自然就带上了为边缘人群和阐释社群辩护的意义,与反抗主导意识形态的立场正相配合。粉丝身份不断在大众媒体的叙事中遭到他者化和病态化,而通过直接的访谈以及人类学民族志,这一代学者让粉丝在学术研究中表达出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观点理念,例如卡密尔·培根-史密斯的民族志著作《进取的女人们》便是深入粉丝圈实地的社群生态描述[5],而另一方面,很多研究者本人就是粉丝,他们自己的见闻和立场也可以作为佐证,让学术界了解粉丝社群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生产流通方式等等。亨利·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就是其中最著名也极具备代表性的案例,詹金斯作为粉丝日常观看电视剧和电影,也在著作中描述自己的文化生活习惯,包括如何观看电视剧,如何与其他同好交换获得电视剧的录影带,如何参与集体放映活动,如何在粉丝同人展会上参与集体活动等等,著作中的许多观点也是他作为粉丝在观看和学习,或与其他粉丝的交流中获得的[6]。而“学术粉丝”这个概念,描述的正是这种多重视角的立场、身份和研究方法。
第一代粉丝研究的著作多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持明显的正面描述和颂扬立场。很多被主流社会他者化的群体开始被主流关注到,在主流文化渠道中开始发声时,他们采用的身份政治叙事也常常就是这样的立场。虽然很多第一代的研究者也会偶尔提到粉丝圈出产的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立场问题(例如,康斯坦斯·彭利就指出,同人社群中的耽美写作和美国文学中的跨种族男性同性社交有清晰的对应关系,而后者也可以理解成为对跨种族婚姻和混血儿的恐惧[7]),但整体上,他们会把粉丝社群理想化,视作一种和主流社会完全相异的乌托邦社群,通用非资本主义的礼品经济,互利互惠,宣扬共享,宣扬平等。到了第二代粉丝文化研究者时,他们就不再需要在一切学理讨论之前首先旗帜鲜明地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立场。究其原因,有第一代粉丝文化研究学者的贡献,但也是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的整体变化所致。20世纪90年代之后粉丝文化渐渐开始在互联网上安家,粉丝文化随之走入大众主流的视野,甚至开始进入媒体工业的生态链条,粉丝圈的污名化状况因此得到极大的改变。在这种条件下,学者就可以关注一些第一代粉丝研究学者出于策略原因不能或者不愿意触及的问题,例如一些不那么美好和乌托邦的表现,如粉丝圈内部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差异等等。这一代学者反对将粉丝社群从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与其将“美好的”粉丝圈看作身处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作为主张平等互助的礼品经济小社群看待,第二代粉丝文化研究学者更倾向将粉丝社群看成整个社会权力关系、社会文化资本差异等级的缩微化体现。第一代粉丝文化的研究者往往避之不提的粉丝圈阴暗面就开始不忌讳地进入讨论之中,例如“反粉丝”(按照中文粉丝圈的术语,即“黑”)、粉丝圈的“鄙视链”、粉丝写作和想象中猎奇阴暗的一面,等等。
按照格雷、桑德沃思和哈灵顿的划分方式,第三代粉丝研究的特点是:在第二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进入细节和具体文化情境,研究呈现出视角和课题的多样化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课题的越发多样化,而且对粉丝的基本定义也有建立在质疑上的拓展,同时,更有语言文化上的拓展。例如,最早一批的粉丝研究学者大多只讨论喜爱和消费流行影视的粉丝社群,即所谓“媒体粉丝”,但是在新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会关注一些其他粉丝社群,如体育粉丝、音乐粉丝等,也关注同人创作之外的文化消费方式,如收集和角色扮演等等。然而,在语言文化多样性层面,却并没有显著的拓展。当下英语学术界粉丝文化研究中,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流行文化粉丝相关的研究仍然占绝大部分。当然,这也受制于参与研究和写作学者的个人身份:粉丝文化研究尤其需要参与者本人的知识系统和情感经验,因而没有直接参与和了解非英语粉丝圈经验的学者就很难更进一步地拓宽视野和研究。
虽然格雷、桑德沃思和哈灵顿的总结和代际划分写于2007年,但是此后的十多年以来,第三代粉丝文化研究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以这样的代际划分讨论粉丝文化研究的历史仍然是准确的。这三代粉丝研究学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体现了对“学术粉丝”这个概念的理解及其研究方法的变化。
二、学术粉丝的立场和伦理意义
上文中所述三代粉丝文化研究学者中,第一代的亨利·詹金斯是英语粉丝文化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著作《文本盗猎者》出版于1992年,以他自身在粉丝圈内的活动和知识展开讨论和理论分析。具体说来,《文本盗猎者》中,詹金斯大量引用粉丝社群中的分析和常见话语,用一些粉丝社群内部的行为逻辑和话语直接破解大众媒体的偏见。例如,詹金斯认为,大众媒体中的刻板印象常把粉丝刻画成心智不成熟的人,无法区分现实生活和虚构的影视文学作品,而这多半是对粉丝言论的一种误解。因为以谈论实际生活的方式谈论影视剧中的虚构情节是粉丝对文艺作品的一种理解方式。[8]粉丝将自我的情感投射入故事之中,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和争论虚构故事中人物的境遇和行为。如果不在粉丝的讨论语境中,心怀偏见的旁观者有时便会忽略粉丝具体争论中细节要点的重要性。学术粉丝的视角因为兼具两种背景和观察范式,因此在粉丝文化研究发展的早期,面对学术界非粉丝群体的质疑和鄙薄时,能起到很好的破除偏见的作用。同时,作为内部人士,学术粉丝也更容易接触到亚文化群体内一些口耳相传的说法和较少有记录的传统,也更容易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研究方式便完全异于外来的自居观察者的学者。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指出,在文化研究领域,流行文化是一种不能进入课堂的特殊知识领域,而在流行文化的投入和热情则往往被目为妨碍学术合法性的因素。社会的知识和权力秩序决定了哪种和文化产生关系的方式才是合法的。[9]格罗斯伯格同时也指出,情感(affect)是粉丝文化的基础之一。情感并不产生自文化内容本身,而是来源于粉丝观察到的文化细节的差异,以及发掘不同之处的能力。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商业流行文化已经成了人们唯一可以呈现和表达不同之处的领域。[10]也就是说,粉丝文化是一种来自情感投入的文化形式,在消费社会的商业流行文化中寻找到的特殊性,通过人们投射的情感产生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也就意味着:“情感投入导致不客观”的判断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研究者的主观情感介入,与其在研究中忌讳情感,不如承认并研究它。
“学术粉丝”的概念之所以重要,也正是因为它指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方式和样态,它承认研究者可以既是粉丝社群中全情投入的爱好者,也同时能熟悉文学和文化理论,可以对粉丝社群的现象和文本进行有效分析。由此,有关粉丝文化的研究就成为研究者对自己所处人群的自我民族志,同时也就必然会带来身份代表和伦理的争论。这种伦理争论在以往的民族志中也不鲜见。简单说来,作为学术粉丝,需要处理自我和身处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达菲特(Mark Duffette)所言,所有民族志(包括自我民族志)都会涉及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是将社群中日常生活的细节翻译成大众能听懂的语句,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学术粉丝的立场意味着学术粉丝比大众更加了解这个社群,负有翻译的责任。当然,因为粉丝文化现在已经悉数迁移到互联网上,“大众不了解粉丝文化”的假设未必符合实际。但是学术粉丝依然意味着更多的知识、义务、可信度、敏感度和经验。[11]这也就自然指出了学术粉丝的义务:他们需要尊重自己的社群,也为学术严谨性负责。
粉丝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女性主义研究,这不仅因为参与粉丝文化,尤其是同人创作的人大部分是女性,更是因为这种研究带有为边缘群体发声、正名的任务。女性主义研究和酷儿研究等领域为粉丝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而性别研究中关于“个人即政治”的理论立场,进一步为粉丝文化研究常用的自我民族志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尽管存在这样显著的理论视角转向,而且当代几乎所有关于粉丝文化的论文里,作者都不再会隐瞒自己是粉丝的事实,但是“学术粉丝”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并不稳定。2011年,以亨利·詹金斯、苏珊·斯科特(Suzanne Scott)、路易莎·斯特恩(Louisa Stein)、山姆·福特(Sam Ford)等几十名从事粉丝文化研究的学者和少部分媒体从业人员一同进行了一场关于“学术粉丝”身份和概念的讨论,这次讨论中出现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立场和观点。[12]一部分学者认为“学术粉丝”已经不再是一个必需的范畴和概念,因为随着对学术研究中情感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使学界意识到,无论怎样的学术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情感投入,因此特别强调粉丝文化研究中的“情感”似乎画蛇添足。这些学者还认为,粉丝文化已经不再受到污名化,所以也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学者个人的身份。例如,威尔·布鲁克(Will Brooker)就认为,他的身份和立场可以直接从他对他研究的蝙蝠侠的详细知识中显现出来,不需要特别从言语中强调。而很多关于“学术粉丝”的困境和挑战也是学术圈整体都会面临的问题[13]。甚至会有一些学者认为,“学术粉丝”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范畴,将具备学术知识的学术粉丝的文化权力置于普通粉丝之上,使得普通的粉丝和消费者无法顺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学术粉丝”这种混合概念和立场在研究中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强调该身份的伦理和责任。克里斯蒂娜·布瑟(Kristina Busse)警告说,虽然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发展,然而关于粉丝文化研究仍然会有涉及伦理的问题。[14]例如粉丝发表在自己博客上的小说创作,虽然公开发表在网上,但在粉丝的语境中仍然是较为私密的写作,所以在引用和分析时理应征求原作者的同意。学术粉丝必须不能忽视自己研究的对象的不适感;而在诚实严谨地研究粉丝文化和尊重粉丝的感情中间,也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当然,传统的文化观念等级秩序依然强大有力,很多人依然因为喜爱某种不具有文化资本的文化产品而受到歧视和嘲笑,“学术粉丝”视角仍然能够提供一种有力的自我正名和论述的视角。
上文所述第二代粉丝文化研究代表性的学者,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阐述“学术粉丝”这个概念时有效指出了“学术粉丝”概念和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陷阱。他认为,同时身处粉丝圈和学术世界并不一定能保证做出的研究和论述一定更具有洞见性[15]。从这个意义上,他否定了身份政治式代言的合理性。他在著作《粉丝文化》(Fan Cultures)中多次反复阐述“打破道德二元论”的核心逻辑。[16]他指出:粉丝文化的研究者很容易进入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譬如,把具有某种特征的群体视作粉丝,他们反抗邪恶的资本,所以粉丝是道德的,资本方则相反;好的粉丝是反抗的、从事同人文本生产的、积极的粉丝,而相反,如果粉丝不反抗,不参与文本再创作,只做消极的接受者,则会被视为“坏的”粉丝。这类逻辑和论断是粉丝圈文化中,也是粉丝文化研究中的常见陷阱。正如希尔斯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依靠一种单一的行为和标准将人群分门别类,并迅速地为他们赋予价值和善恶对错的道德判断。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会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同时参与社群生活和消费方式,简单一刀切的讨论对于我们理解粉丝文化的现象并无助益。而警惕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方式,同时也是在提醒学者不要在研究中做出过于简单绝对的评价。因为粉丝文化研究部分致力于将一种被污名化的现象拯救出来,所以必然需要强调其积极一面,以打破其社会普遍刻板印象,而同时,粉丝文化中自然也存在符合刻板印象的现象和行为。也就是说,虽然大众媒体并不应该将所有的粉丝都看作在演唱会上尖叫晕倒的疯狂粉丝,或者为了接近自己喜欢的明星而骚扰他们的跟踪狂,但这样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在粉丝中依然存在,那么是坚决否认这些行为,并将其从理论体系中摒弃出去,还是接受这样早已被污名化的行为并将其一并理论化?在希尔斯看来,学术粉丝的身份就是这样在不断地建立和挑战道德二元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后来的讨论中,希尔斯进一步指出,学术粉丝的意义在于多重的自反性,需要身处多个共同体中的学者对每一个身份和共同体都保持警醒和批判。[17]这也就是说,学术粉丝的力量更多来自研究过程中的自省和冷静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身份和价值判断。
三 、“学术粉丝”个人化研究范式的局限和挑战
虽然粉丝文化研究总是植根个例和较小范围的观察,但是因为情感联系的共通,却往往可以拓宽其适用范围。然而即便如此,在挪移具体语境后,我们也需要小心分辨理论和分析的适用性。另外,粉丝文化非常庞杂多样,产生的文本也数量巨大,而且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在不同的呈现媒介和平台上都可以存在,所以即便试图放宽视野,也总会有看不到的社群、成员、历史脉络等等。这时对粉丝社群和文化进行总体性描述和概括,必然会呈现选择性的结果。正如桑德沃思对詹金斯和培根-史密斯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詹金斯因为身处波士顿的大学城(他写作《文本盗猎者》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平时见到的也是波士顿受过高等教育、政治立场偏激进的粉丝人群,而培根-史密斯则是在美国的乡村地区做民族志调查,见到的人自然也就没有那么激进的政治立场。[18]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导致詹金斯对粉丝文化的定位格外浪漫,充满了平等和互助的乌托邦色彩,而培根-史密斯的态度立场则谨慎而模糊得多,她也是第一代粉丝研究学者中为数不多的直接指出粉丝圈问题的人。此外,从研究者主要采用的例证和研究的视角,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本人所在的粉丝圈是哪一个,主要的观察经验和情感经验又来自何处。例如最早一代的詹金斯、彭利、培根-史密斯等等,对美国科幻影视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渊源,而希尔斯则对“邪典”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桑德沃思很明显更加熟悉同人写作较少见的体育粉丝和音乐粉丝圈,这就令他们的视角各自不同,而得出的理论,也可以显现出各自熟悉的粉丝文化领域的特征来。例如,桑德沃思分析粉丝所热爱的对象,认为这些对象会产生“符号中性化”(neutrosemic)现象[19]。这个结论应用在一些阐释空间更大,文本书写更自由的粉丝对象,如球队、运动员、歌手形象的解读上,是更加合理的。在消费者阐释空间相对狭窄的领域,例如影视剧情上,这类分析就需要细加分析和辨明。桑德沃思认为粉丝可以将自己喜爱的对象阐释成各种完全不同,甚至相悖的意义,虽然在实践中多有案例,但是这种符号本身也必须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由于英语世界中粉丝研究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因此事实上已经造成几个流行文化文本成为研究时的惯用文本,例如《星际迷航》《哈利·波特》和《吸血鬼猎人巴菲》等等。[20]这种代表性应当成为对“学术粉丝”研究方式的反思,即:如何破除少数文本和人群代表全体的代表性问题?如何在这些经典流行文本及其相关论述之外获得话语权?在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上,文化特殊性限制向来极为重要。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将欧洲还原为普通地域”、将西方理论重新回归特殊语境、使其不再占据“普遍化”理论高地的倡议;在文化研究中则更需要注意论述和结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挪用可行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有相当成熟且历史悠久的娱乐产业,而更换语境,如在中国社会中,则必然有所区别。中国流行文化中存在大量的外来成分,无法形成完全自足的本土娱乐文化,粉丝圈的交流和构成方式也相对较为复杂多样,通常需要更深的投入和知识才能详细了解。与之相伴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谨防“我见即世界”的轻率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固有的性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等级产生的权力差依然在发挥作用,“代人写史”的现象存在,而同样会有占据学术圈文化资本高点的学者轻易地为自己并不了解和认同的社群代言,这是特别需要认识和纠正的。
尤为令人担心的一点,也正是现在正发生在中文网络的事实,是女性粉丝圈的再度边缘化和不可见化。西方粉丝文化研究大多重点讨论女性粉丝主导的媒体粉丝圈,将同人写作等粉丝创作看作粉丝研究的核心讨论对象,而在中国,这方面现有的讨论和材料都相当不够。因为女性粉丝圈和同人圈更游离于主流文学和文化圈之外,出于自保的原因,往往不会特别积极地寻求主流文学文化圈的认同。同时女性粉丝圈自己也未必会将自己的文化实践作为上得台面的严肃创作,记录和保存的意识不强高。当下的电子时代又被戏称作“电子中世纪”,正是因为网络时代数据消失比我们想象中要频繁得多,而且往往不可预料且不可恢复。随着网站关闭、数据丢失状况不断扩大,很多粉丝圈的实践就此遗落消失。而女性粉丝圈由于社群封闭,交流准入的障碍也高,很多粉丝的写作就极易丢失和被遗忘,这就导致了大量以男性粉丝社群视角“写史”为名的文字记录会将女性写作和实践彻底忽略。这就特别需要鼓励和强调边缘社群的介入和主动的自我书写。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来,在社会逐渐分化,按照消费兴趣和品位逐渐形成新群落的当下,以个人实地亲身的体验抵抗一些大而无当的大叙事,可能是更真实有效的。
正如安妮·库斯特里茨(Anne Kustritz)所指出的那样,学术粉丝应当包含更丰富的含义,而不是只指向文化研究中某个特殊的采用相似研究方式的群体。在粉丝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并不共享类似的经验,他们更多共享的是一种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使研究的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和角度介入粉丝研究的学术传统;而另一方面,这个词汇也描述了一些学者与自己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21]。换句话说,虽然这个概念至今没有严格的受到普遍承认的定义,学术粉丝同时作为一种概念和研究方式立场,仍然以其多层面多角度的阐释可能性在粉丝文化研究领域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这种特殊但也普遍的研究方式也给整个学术圈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考,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研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作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需要从中吸取进行在地化研究的经验,但也要克服相应的代表性问题,以期为粉丝文化研究,乃至整个文化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填补研究空白。
【文献引用格式】郑熙青.学术粉丝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自粉丝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挑战[J].百色学院学报,2020,33(03):24-30.
注释:
[1]Adorno,Theodore and Horkheimer.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89.
[2]Gray,Jonathan,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Introduction: Why Study Fans? In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Eds. 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1-16.
[3]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174.
[4]Fiske, John.“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The Adoring Audience. Ed. Lisa Lewis. London: Routledge, 1992:30.
[5]Bacon-Smith, Camille. Enterprising Women: Television Fandom an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Myt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6]Jenkins,Henry.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7]Penley, Constance. NASA/TREK: Popular Science and Sex in America.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7:125-145.
[8]Jenkins, Henry. Textual Poachers:Television Fans &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107-119.
[9]Grossberg, Lawrence.“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The Adoring Audience. Ed. Lisa Lewis. London: Routledge, 1992:50-51.
[10] Grossberg, Lawrence.“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The Adoring Audience. Ed. Lisa Lewis. London: Routledge, 1992:59.
[11]Brooker, Will, Mark Duffett, and Karen Hellekson. 'Fannish Identities and Scholarly Responsibilities: A Conversa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Fandom, 1st ed. Routledge, 2018:63-74..
[12]详见亨利·詹金斯的博客:Confessions of an Aca-Fan: The Official Weblog of Henry Jenkins. http:///.
[13] Brooker, Will, Mark Duffett, and Karen Hellekson. 'Fannish Identities and Scholarly Responsibilities: A Conversatio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Fando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63-74.
[14]Busse, Kristina.“The Ethics of Studying Online Fandom.”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Fando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9-17.
[15]Hills, Matt. Fan Cul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6]Hills, Matt. Fan Cul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7]Gray, Jonathan, Matt Hills and Alisa Perren. 'Aca-Fandom and Beyond: Jonathan Gray, Matt Hills, and Alisa Perren (Part One).' Confessions of an Aca-Fan:The Official Weblog of Henry Jenkins,29 August 2011,http:///blog/2011/08/aca-fandom_and_beyond_jonathan.html
[18]Sandovss, Cornel.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5:27.
[19]Sandovss, Cornel.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5.
[20] Sandovss, Cornel.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5:27.
[21] Kustritz, Anne, Louisa Stein and Sam Ford.“Acafandom and Beyond: Week One, Part Two (Anne Kustritz, Louisa Stein, and Sam Ford).”Confessions of anAca-Fan: The Official Weblog of Henry Jenkins. 20 June 2011,http:///blog/2011/06/acafandom_and_beyond_week_one_1.html.
作者简介


郑熙青(1984~ ),女,江苏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文学人类学组稿编辑 | 黄 玲审稿编辑 | 梁 昭值班编辑 | 地 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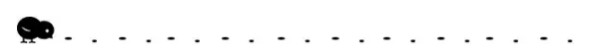
在田野中发现,
在书斋中思考,
在交流中完善,
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主办,
实时更新讲座、讲读会信息,
分享书评、影评、摄影、田野报告......
网址:【学术观点】郑熙青:学术粉丝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自粉丝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挑战 https://mxgxt.com/news/view/354709
相关内容
数字时代的破圈:粉丝文化研究为何热度不减认同与表演: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研究
粉丝文化亟须深入研究与正确引导
明星粉丝群行为规范化治理研究
核心粉丝是如何炼成的——基于文化资本视角下的粉丝社群研究
“粉丝文化”与明星真人秀节目关系研究
MBAer研究所第十一期:中国偶像明星粉丝及粉丝经济研究
虚拟偶像粉丝的参与式生产行为研究
圈地自萌—明星CP粉丝的圈层文化研究
“饭圈文化”影响下粉丝群体的网络民族志研究——以朱一龙粉丝群体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