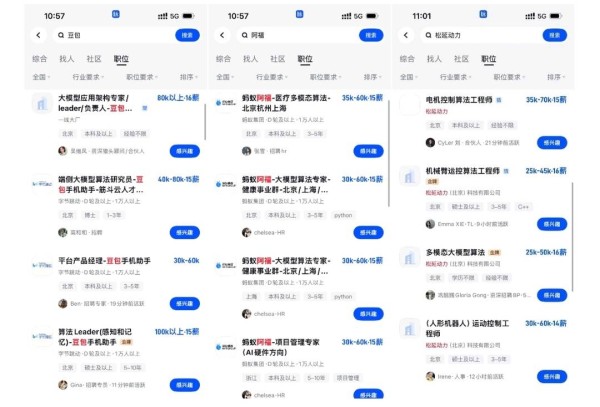匠作、创作、受宠与受缚 ——【书评】《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刊载于4月6日《音乐周报》 作曲家的身份是什么?这是一个既为人所议论,也被作曲者自己所关心的话题。一直以来,它的定义如在云里雾中,普通人概念里,那群“艺术家”时而是不食烟火的创作者,时而竟又成了仆人或革命家,好像有时,还是饱一顿饥一顿的苦命人? 本书讨论的正是这一话题。作者夏滟洲专于音乐史学和社会学,200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单看书后长达十几页的文献引用清单,就知道他锻造这份“小题大作”的用心良苦。 书中前半部分提到,中世纪歌曲多以口头方式传承,诗人、作曲家和演唱者常是同一人,他们往来服务于贵族,部分有荣誉称号, 部分得委任职务,依赖诸侯的资助和恩宠。 西方最早的“composer”,就字眼意思更多的是将素材“拼接到一起的人”,具备强烈的匠作特征,而个性甚弱,反倒是游吟诗人更配得上“创新之人“的称号。 随着记谱法的普及、教会体制对音乐的提倡,“假借记谱艺术的多声部音乐“决定了严格意义上作曲家的出现,从马肖开始,我们陆续有了杜费、奥克冈和若斯坎。在不同地区,作曲家获赞助的形式也不同。书中所列的巴赫工资详单,以及对现状大发牢骚的记录,反映出赞助制度下音乐家的地位竟是如此的低微,哪怕是堂堂的巴赫,也不得不在教堂、宫廷、教堂-城镇三者间周游。泰勒曼的处境则较好, 每年薪酬1600马克,不过义务是:每周写出两首康塔塔,每年一部受难曲。 歌剧行业不久兴起,一个建立在盈利基础之上的市场很快成型,必然带动了作曲家经济独立化的趋势,17世纪音乐的商品雏形甚至让演出变得比作曲更重要。 17世纪的音乐会活动多以家庭、教堂和大学社团为中心,此后则以贵族、半私人或公众的音乐会为主。而到了18世纪末,一系列革命对国王贵族的旧秩序提出挑战,音乐从宫廷贵族的玩物向市民阶级自然情感的表达过渡。于作曲家而言,贵族的保护虽未立即中断,委约创作的比例还在,但选择无疑更多了——或靠作曲-教师兼职挣取报酬;或兼作演奏家-指挥家,在管弦乐队谋求生活;或去试着做企业家,如经营歌剧院等等。 贝多芬的年代,正值欧洲革新精神萌发时,新兴市民文化对人性标榜颂扬,此其一;其二在于成熟的器乐音乐会是音乐进一步自立的标志,因为它们比声乐的曲目更众,还需系统的节目单和适量新作品供给。书中认为,贝多芬正是凭借这两点弘扬了他“纯音乐”的理念,正应他自称的“音响艺术家”(Tonkünstler)或“音响诗人”(Tondichter)——不是“作曲家”哦! 其时他真可谓霸气侧漏:“每个乐谱都有六七家出版商要出版,只要我愿意,多少出版商都能找到,他们已经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多少,便付我多少......”,此时的他,既可以凭一己之意志写高雅的东西,又可以趋时写一些应景之作,不亦乐乎。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和鲁道夫大公的资助关系之外,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等具有现代体制特征的保护人,也算是有标杆意义了。此时的贝多芬,可以说在一种“公开的吸引力和保护下”表达了他真正的艺术诉求,诸此种种运气,不仅让早逝的莫扎特望尘莫及,同一社会环境下的羡慕者也多得是。 贝多芬之后呢?“音乐商品”的意义无疑进一步凸显。书中有言,音乐之商品化何尝没有负效应?当市场力量控制音乐生活,作曲家抽身去尝试一些有风险的事情,做得好还行,做得不好,就让位于了明星制度和金钱游戏了,而民众间,过去纯朴真诚的欣赏环境已被打破。他们于是迈入两难境地:要么屈就公众,要么自顾自创新。想要平衡吗?得有很强的适应力才行,能在大潮中“幸存”下来的真才杰毕竟仅是少数。 当年指挥家魏恩加德纳一句慨叹,算是替经济大潮之外的那些踽踽独行者说了话:“想想布鲁克纳吧,就这样毫不动摇地沿着他的路朝既定目标走去,深信不会受重视,除了失败外,一无所得。较之每天获得成功与得到广告宣传的时髦作曲家,他正无比精细地处理着琐碎小事。我们应向这样的人鞠躬致敬。”
网址:匠作、创作、受宠与受缚 ——【书评】《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 https://mxgxt.com/news/view/816909
相关内容
论作曲家与作品的“伟大性”问题作家与创作:作品与作家经历的关系及作家的创作态度
社会生活与作曲家的情感倾向
钢琴巨匠鲁道夫·布赫宾德四月来津演绎贝多芬与舒伯特传世经典
批评家与作家应该成为诤友
两会她故事 | 韩再芬:创作更多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优秀文艺作品
论述贝多芬的音乐成就及影响。
贝多芬的音乐艺术成就.pdf
从拔牙匠到作家富豪,活着就是信仰
贝多芬人物传记.pp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