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看得见”的语言——论梅子涵晚近散文集《黄麦地》

【摘要】梅子涵从事文学创作近 50 年,在散文语体和题材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一种基于平等理念的创作,交织起儿童和成人不同的思维方
式,以自觉的“看得见 ”形象捕捉,彰显了主体特色,扩大了创作视野,给他的散文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梅子涵的主体位置,在散文的每一篇都清晰可见,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非常“ 自恋 ”的人。这种“ 自恋 ”既是对人的特征,也是对他散文基调的概括,是儿童化思维方式的体现。
【关键词】黄麦地;梅子涵;主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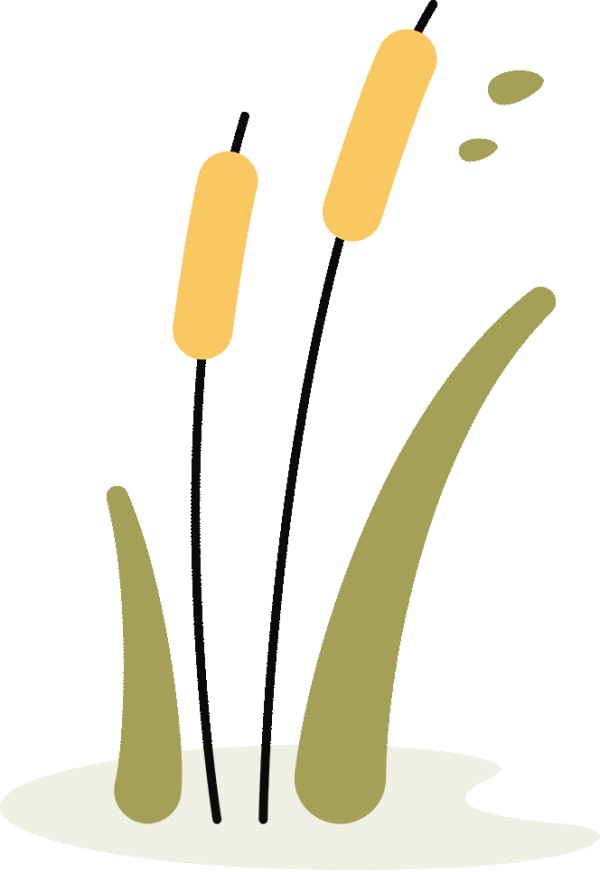
一、散文的“看得见”
梅子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写作,写小说、写散文迄今已近50年。晚近时期,他继推出散文集《绿光芒》后,又出版了散文集《黄麦地》,形成前后呼应的系列。
如果从他小说和散文的异同角度展开,首先可以谈文笔的共同点,这是把他的作品看上几段就能感觉到的。一个对文字稍有领悟力的人,能够从一堆作品中辨认出梅子涵的文笔。不管小说,还是散文,他的文笔都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即“梅氏风格”。早在20多年前,儿童文学评论家周晓在回顾建国50年的上海儿童文学创作时,便对梅子涵“强烈的文体创造意识”以及跟新文体紧密相关的“叙述语言的新尝试 ”大加赞许。
如果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那么梅氏语言风格的形成,就是梅子涵创作成熟的标志。这其实并不容易,有些似乎名气比梅子涵还响的作家,其语言的辨识度远不如梅子涵。评论家吴其南在论及梅子涵小说时,也认为“很容易感到一种只属于梅子涵个人的语体方面的东西”,而这种辨识度,在他的散文中体现得相当鲜明,且具有特别的意义。
作家殷健灵曾谈到,有些作家小说写得很好,但散文创作并不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我们一些人的认知中,写小说要比散文困难得多。
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有些作家对散文文体比较轻视,认为散文是文类中的小品,比不上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所以对散文写作投入精力不够。笔者曾经听到不止一位作家说过,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就是颁给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的,凭借散文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如果有些作家对语言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对自己遣词造句的能力缺乏自信,是不敢发表太多散文的(如果其对从事文学创作有崇高使命感的话),尽管也有不少作家以契诃夫“大狗小狗都要叫 ”的理由来为自己不断推出不成熟的散文作品辩护。相形之下,小说主要是靠编故事来吸引人,语言的薄弱、不成熟,读者往往忽略不计,但散文则不行。一般而言,当既没有吸引人的叙事也没有独特景物书写的散文呈现到读者面前时,语言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语言不行,缺乏吸引人的力量,读者就不爱看。
当然,这是从一个泛泛的角度来说,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误解,好像语言可以从所要表达的内容中剥离出来,仅靠一种纯粹的、近乎透明的语言就能打动人。事实不是这样,梅子涵的创作重新理解了“生活与文学 ”的关系。从他创作的小说和散文的不同文类来看,梅子涵的小说是把生活放在文学中,而他的散文则倒过来,把文学放进生活中。
同样是生活和文学的联系,对于小说,梅子涵用文学的框架来装生活,或者说,小说成了他直接书写生活的“保护伞”,真人真事,他本人、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细节,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并在小说的整体框架中完成形象的裂变,构成生活中的梅子涵,处于写作状态的梅子涵,以及进入小说作为一个人物的梅子涵,具有多重性。而梅子涵的散文,用生活的框架来装文学,文学的场景再现,或者一些生动细节因为处于生活之流中的散文作者的真诚表达而让文学的诗意从生活中散发出来。
梅子涵通过结构互换的特点呈现,打通了文学和生活的二元对立关系。生活和文学的这种紧密关系,曾被评论梅子涵小说的吴其南称作“一种很别致的创造艺术世界的方式”,而体现于散文中的就是“一眼看得见”。

讨论梅子涵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黄麦地》,也许应该参考一下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散文创作的。《黄麦地》里收录了一篇他以《散文》为标题的散文。他会像莫里哀的戏剧《贵人迷》里的人那样谈论吗?按照《贵人迷》里的说法,我们嘴巴里说出的都是散文。这话当然带有讽刺性,但是不得不说,梅子涵的说话不但似文学意味浓厚的散文,更似引人入胜的小说。凡是跟他有过长谈的人,都会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吴其南从梅子涵“写 ”和“说 ”相融合的方式来讨论梅子涵的小说,认为梅子涵的小说已经锤炼出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那么散文呢?笔者觉得有一个由梅子涵本人概括的意思表达得也很好,即写出来的散文能被人“看得见”。这是在他的《散文》中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他这么说了,也这么实践了。
他写到,在他读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在教室里把讲台前老师说的那个“散文 ”字眼给记住了,而且“从此在我心里端坐下来 ,一眼看得见”。当他这么写的时候,他让读者也看见了:看见他端坐在教室,静静地听着老师在讲课,听着老师在念一篇上海市优秀作文;看到从老师口中流淌出的“散文 ”字眼,像精灵一样静静地在他心里端坐下来。
我们看见一个有点抽象的字眼是怎么获得了一个很形象的“坐姿”。在这里,他如果说“从此我心里就记住了”,那不是文学的表达;如果说“从此在我心里坐下来”,这才是文学的表达;但当梅子涵说“从此在我心里端坐下来”,就成了梅子涵的表达。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单有文学的形象,还有一种神圣感、使命感,把散文写作的使命感带入生活,带入一个还是孩子的人心里,这就不是简单地坐,而是端坐,是端庄、端端正正地坐,坐得很安稳。这种端庄、端正,跟梅子涵以后的创作拒绝庸俗、拒绝迎合市场恶趣味的倾向联系在一起(这跟某些在图书市场大红大紫的儿童文学作家有鲜明区别)。
可以说,梅子涵的散文创作很早就带着这种神圣感、使命感,让他本人,也让我们每一个读者都“一眼看得见”。这个“一眼看得见 ”成了理解他作品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他说的“看得见”,有着文学和生活 “看得见 ”的印证,是语言的“看得见”,也是生活的“看得见”,是笔下有人的“看得见”。特别是“看得见 ”那个执笔之人,“看得见 ”作者的主体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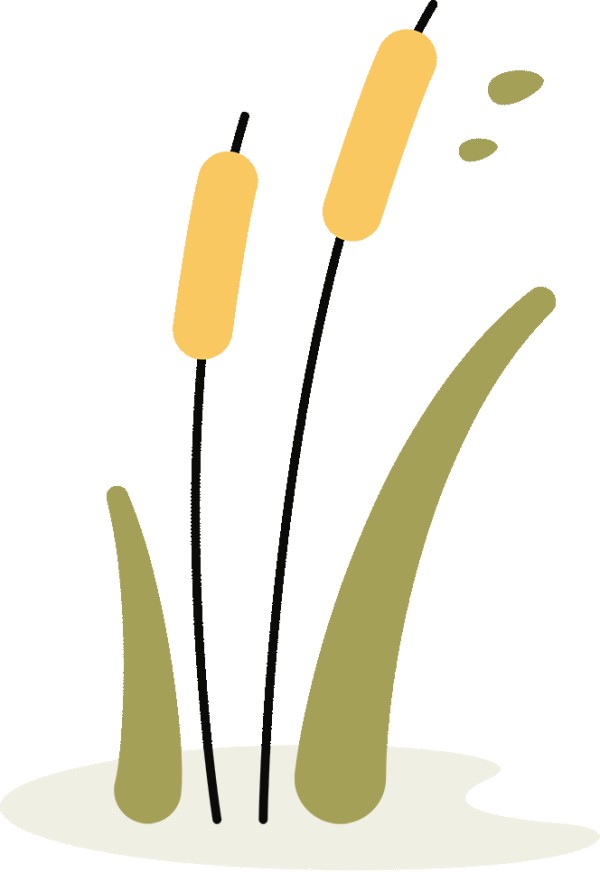
二、看见人,看见文
以前笔者和黄清合作讨论过梅子涵小说的主体性问题,在梅子涵的散文中,这个主体性更清晰。
在小说中,主体意义上的“我 ”基本上是隐藏起来的,即使梅子涵的小说中有不少采用了第一人称,但就像前文说的,生活中的“我 ”进入小说,已经发生了裂变,主体的“我 ”躲在了虚拟的叙事者“我”背后 。而他的儿童小说就是假定了作为未成年“我”的叙事者,跟儿童时代的梅子涵拉开了距离。所以在小说里,读者看到的作者主体更多是经过化妆打扮以各种面貌出现的。说得夸张一点、动听一点,我们可以说这种裂变,体现了佛一身而化作亿万身的境界。不管他在小说里化作怎样一个成人或者孩子,跳动的心还是梅子涵的。
但散文不一样,散文没有这样的化妆,梅子涵的主体位置在他散文的每一篇中都清晰可见。他心目中对自己有一个定位,直率一点说,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在散文中可以清晰看到他的自恋性,在小说中却有点朦胧。
在这里,“自恋 ”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人的特征,也是他散文基调的概括。这种自恋是儿童化思维方式的体现,或者说是从儿童思维特征中发展出来的。对于儿童思维,同样不能加以幼稚化的理解。对于儿童思维特征及其以后的发展,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做过一个解释。当有人问他何以会有那么大成就时,爱因斯坦回答说,他只不过是把他小时候好奇的问题一直保持到成年继续思考,所以就有了一点成就。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5岁的时候,对指南针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好奇。因为指南针的行动不是让他看到了这是具体物体直接接触的结果,而是让他发现完全不符合他当时认识到的事物位置该有的规律,“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这跟爱因斯坦后来坚持研究时空的隐含物理关系、那种“超距 ”作用,以及孜孜以求“ 同一场论”,有一定关系 。直到他74岁回答记者提问时,还强调了这一点。
此外,爱因斯坦也从成年人的立场,对儿童思维特征进行了回溯。他对一位传记作者解释:为什么恰好是我创立了相对论呢?当我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原因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完全不考虑什么空间和时间问题。照他看来,这个问题他在小时候就想清楚了。我呢,智力发育如此缓慢,以至于当我已经长大的时候,空间和时间还盘踞在我的头脑中。自然,我能够比儿童时期发育正常的人对问题钻得更深入一些。
很多人在童年时候思考的比较玄虚的问题到了成年就丢掉了,如爱因斯坦说的,是自以为想清楚了,或者兴趣转移了,或者有了更多务实、功利化的思考。爱因斯坦说的对儿童时代兴趣的持续保持,笔者觉得在梅子涵创作时体现的思维方式及他散文中是看得比较清晰的。
梅子涵喜欢表现自己的骄傲,比如他在散文《鼓点》中写到拥有一支昂贵金笔的骄傲,那种毫不掩饰的骄傲是小孩子才有的炫耀心理。成人后,有人会为这样毫不掩饰的炫耀感到不好意思,但梅子涵依然毫无顾忌地炫耀着。笔者似乎看到了一种孩子般的天真和骄傲,更看到了笔之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意义。一支金笔,在他手里,可以让文字生出魔力。他会把他从童年时代就拥有的美好、珍贵、价值观大声说出来,让孩子气的炫耀发展为成人的坚守和自豪。这很可贵,使得他至今仍然能够保持创作的活力,并让周边人清晰看见。
尽管《黄麦地》中的散文涉及的许多内容已经不算儿童文学,哪怕梅子涵写儿童时代的自己,也是站在今天的成人立场来回顾的,但是那种儿童思维特征依然贯穿在他的散文中,不经意的一笔,便把儿童的感觉带到读者眼前。
比如,他写读小学时去同学家玩,“那门槛的踏进不会让你胆怯, 跨出去离开也不用客客气气,不用说再见 。这样的门槛真是只有童年才会有,长大后就很难再会有”。这里,梅子涵把儿童之间交往自然而又自 由的感觉放到成人世界里回顾,从很形象也最普通不过的门槛入笔(何其芳的名篇《老人》也写过“专和小孩为难的门坎”),是感觉的,也是反思的。
这一点跟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创作的《一个儿童的诗园》很相似,既以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视角来捕捉童年的生活点滴,也让童年的那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渗透到理智之年龄中,让两者成为彼此取舍后的再融合,达成一种创作的张力。这两种思维方式互相渗透和具有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形成梅子涵语言风格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梅子涵的语言风格都很清晰,不同的读者和评论者都可以概括出他的一些特点:有说是以幽默诙谐著称,有说是淡而有味,有说是不露声色的情感起伏,等等。如果从一个非常简单、大家都“看得见 ”的语言现象入手来谈梅子涵的创作特点,便是文字的重复。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现象太平凡,不断地重复,这不就是小孩子的言语特点吗?小孩子拥有了一件好东西,明白了一个道理,会反反复复跟你说。或者说得更专业一点,用瑞士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小孩子刚开始投入的初级阶段的游戏,就是通过重复活动来达成的一种练习性游戏。读者可以在梅子涵以笔为游戏的写作活动中、在他的文字中,看到这种重复性。这是儿童思维在他笔下的持续延展吗?是,又不是。
他的文字固然有相当多的重复,但在不断重复中,含义在不知不觉地深化,情感在一点一点地充实。所以他的文字在重复中,经得起读者的重复朗读。我们似乎还看到了,梅子涵本人也在这种重复的讲述中,一遍遍回味和一遍遍咀嚼,并把自己的感情带进去。
例如,《黄麦地》收录的《萝卜头》一文中,一个已经习惯了自己驾车的作者,被老同学鼓动着去很有劲地坐公交、地铁,重复着“很有劲的 ”“很有劲的 ”的感叹,那种同学间的朴素情意,就在这重复中,被一点点召唤过来。
《老蓝车》这篇中说到生活待遇,梅子涵把大学老师和卖茶叶蛋的加以比较,在比较中鄙视了某些大学老师的抱怨。当他理解卖茶叶蛋的普通人的艰辛后,写下最普通不过的“辛苦着各自的辛苦,努力着各自的努力 ”句子时,却有着大气的姿态。
这里,用词是如此普通、重复,句子是如此没有变化。如果中学生这样写词句,肯定要被有些教师批评。但若细读,把上下文连起来读一读 、品一品,写得多好!简单、有力,因其简单而更有力,涤荡着一切蝇营狗苟的小声小气——一种旧时代文人叹息中的腐酸气。就像他写下的,“讲着学问的人,讲着文学、历史、哲学的人,还发出那么窸窸窣窣的小气声,那真是学问一点儿也不如茶叶蛋了”。
这样的说法显示出真正的学者 、作家的大气,似乎也有着他流连不去的 、儿童式的较真情绪。他写下“‘忠诚 ’这两个字已经很稀罕了,因为已经不那么稀罕了”,重复的“稀罕 ”背后,引人感叹着生活中的空空荡荡。
梅子涵在简单的重复中,把生活积累下的情感、思想带进去,形成特有的意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那种意境。于是,儿童的简单重复的思维,跟积累起的成人阅历,自洽地融为一体。再比如,《黄麦地》中的《车票》这篇,开头写:
我看了看手表,是晚上七点五十分。这不是一个很晚的时间,可是在一个冬日的乡下公路上,它已经很晚,更是很黑,很晚很黑的公路上只有这一辆手扶 拖拉机“ 突突突 ”开着,我坐在它后面的车斗里。
前一句刚把乡下公路上的那个时刻形容为“已经很 晚,更是很黑”,紧接着写“公路上”,很晚很黑已不言而喻,却还用“很晚很黑”来形容,岂不是重复?重复的还有公路上“突突突 ”的拖拉机声,还有热心送他去农场的陌生的拖拉机手方言中“侬侬”的发音。这不断重复的“突突突 ”和“侬侬 ”声,回荡在很晚很黑的公路上,回荡着的是农村人那种朴实、亲切的感觉。开头所谓的“很晚很黑”,描写农村一种特定情境的氛围,区别于城市的客观环境,通过重复,这种特定情境又向着作者的主观心理世界慢慢渗透。而“突突突 ”和“侬侬”声,似乎可以成为抵抗黑暗的力量,可以从时间之流中升腾起来,并在重复的呼应中,形成音乐般的基调。
非常有意思的是,梅子涵在《散文》一文中,说他写的小说“总有散文般的轻柔和弹奏”。“弹奏”?他怎么会用“弹奏 ”来形容其散文写作呢?如果我们对此感到困惑,只要读读他有节奏的文字重复,便可以理解 。这种文字的重复如同被乐器弹奏出的旋律,既让人感受到情感的深化,也能获得审美的愉悦。
三、“物无贵贱”的看得见
梅子涵散文的语言特点和题材特点相关,二者均被同一种观念统摄。
我们经常说梅子涵是文体学家、语体学家,他在语言方面有很大的创新。但是一个好的作家,绝对不是纯技巧意义上的作家。他的语言一定有一种生活的质感、一种物的质感,让你“看得见”的不仅仅是语言,也是语言携带的物象、那整个的世界。他的语言和物似乎黏合在一起,但是一个好的作家,绝对不是纯技巧意义上的作家。或者说,他的语言像水一样在纸面流淌,多姿多彩的物被携带着一起前进,浩浩荡荡,滔滔不绝。

殷健灵作为《新民晚报》“夜光杯 ”中的“子涵夜话 ”栏目编辑,把梅子涵的散文陆续发表出来,每月一篇。她惊讶于梅子涵能够坚持写 12年,并且还在继续写下去。为什么梅子涵总能找到那么丰富多样的题材?也许写小说还可以,因为小说依托了心灵的想象,依托了雨果说得比天空更广阔的心灵的想象,把一个个故事从无边无际的想象世界中打捞出来。但生活的现实是有边际的,梅子涵也并没有分身术,没有每天活48小时甚至96小时,为什么他能获得如此多的生活素材,让他的散文写作在一个栏目坚持了12年之久?好像他的生活,真成了诗人何其芳说的,是一个无尽的宝藏。为什么?
也许梅子涵对生活的理解和我们不一样;也许这跟梅子涵的自恋有很大关系;也许正是由他的自恋出发,发展出了一种平等意识。因为在梅子涵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他接触的物、遭遇的事、打动的情感,以及引发的思考,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就像他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没有好坏之分。
梅子涵曾对有些学生喜欢摘抄文章中的好词句加以反驳,有的老师和学生也对无法在梅子涵的作品中摘抄到好词好句感到困惑。梅子涵说:“我的好词好句就是你摘出来的那些吗?难道没被摘录的其他词句就是写得差的吗?”“我写下的每一句,都是最好的句子,如果是差的词句,我就根本不把它写出来了。”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样是一种自恋的心态反映,但这种心态对梅子涵语言风格、题材特色的形成很重要。因为自恋、自带光环,所以他把光芒投射到生活中遭遇的每一件物、每一个人之上,让他觉得发生在身边的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是他笔下的好材料 。其中,常常被我们排除在外的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但我们许多人却不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以及遭遇的物和人。我们自觉卑微,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态,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筛选,分出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留下一些重要的,摒弃了更多不重要的,自以为抓住了生活的重点。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可以用来写作的题材已大大缩水。我们许多人成不了作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驾驭不了文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对生活重要性的感受过于迟钝、理解过于狭隘。
而对梅子涵来说,不存在、也不应该进行这样的筛选。他的散文集《黄麦地》是用其中一篇写梵高客居法国的散文篇名来作集子名的。在那篇散文中,梅子涵穿过黄麦地,来到梵高墓前,献上37根青麦穗,对代表着梵高的37年生命,表达了他的敬意。
我觉得在对待身边事物的态度中,在对待生命每一个年头的价值认同中,梅子涵的文笔类似于梵高的画笔。梵高不知疲倦地画下他身边的寻常物——画他穿过的鞋子,画他坐过的木椅, 画他点过的蜡烛,画他爱过的亲人,画他触摸过的向日葵,画他欣赏过的鸢尾花、仰望过的星空,画他凝视并想穿越而又最终长眠其间的黄麦地 。同样,在梅子涵笔下,他所触摸过的、经历过的一点一滴都值得书写。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都有梅子涵自身的情感投射、光芒照耀 。

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他的创作看得过于容易、过于随便,而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境界。梅子涵使用《黄麦地》作为整本散文集的名字,让梵高的精神气息弥漫开来,让读者抓住作者散文创作的根本。
这里可以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来解释两种不同的境界。《秋水》里北海若跟河伯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以俗观之, 贵贱不在己。”
也许我们都是自恋的,只不过有些人的自恋局限于用“物 ”本身来看世界,所以“ 自贵而相贱”,或者任由世俗评价。相反,梅子涵以万物一体的大“道 ”来看世界,所以物没有贵贱。
笔者认为,梅子涵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以道观物,最终因为物无贵贱,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值得被看见、被书写下来,每一样东西都是能够放光的,从而让他的写作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些人自恋中的“自”是“小我”,而梅子涵自恋中的“ 自 ”是“大我”,携带着周边许多物和人的力量。但是,“大我 ”仍以“我 ”为前提,把“我 ”放在其中,由“我 ”的情感来笼罩。
正如他前一本散文集的集名《绿光芒》所暗示的,他把自己的情感光芒从所写之物中折射出来。“物皆着我之色彩 ”是梅子涵风格形成的标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未必不是他的一种局限。如果重返上引《庄子》中《秋水》篇的那段议论,紧接着还有“以差观之 ”“ 以功观之 ”“ 以趣观之 ”等 。而“ 以差观之 ”则是这样说的: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秋山也,差数睹矣。
这提醒我们,伦理意义上基于平等观念的对他人他物的尊重,也有可能被误用,导致对不同人与物差异性的等量齐观,乃至对他者的个性遮蔽。安徒生在童话《区别》中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人们对多样性的美好事物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不同事物分出了地位高低。
梅子涵在《小蓝车》中 以“忠诚 ”和美好串联起他舍不得淘汰的、过时的旧轿车——他的“老蓝车”,这种过时和老旧以曾经的“牛 ”和“倜傥 ”留存在他的美好记忆中。这种娓娓道来的感情和满溢的美好固然感染了笔者、打动了笔者,但是,笔者总觉得生活中还有另一种美好、一束不带光芒的情感、一个似乎尚未看见的“他者”,从老蓝车边上的边上或者背后伸出手来, 向我们打招呼。
总而言之,梅子涵以他语言中的“一眼看得见”,让读到他散文的人、受到他感染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对生活,以及生活中曾忽视的人和事投去了新的目光 。同时,他让我们理解了,当他执着地把文学带进生活时,可以给生活中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心灵世界带来怎样的意义。【END】
文/詹丹,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教授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点亮小星标 ★ 精彩不错过
责任编辑:
网址:“一眼看得见”的语言——论梅子涵晚近散文集《黄麦地》 https://mxgxt.com/news/view/6118
相关内容
“一眼看得见”的语言——论梅子涵晚近散文集《黄麦地》梅子涵:二十年的明亮全是动情
徐扬生散文集《黄昏的神仙湖》新书首发
重庆作家文猛散文集《河生》出版
为什么说中文是世界语言的压缩包?
寻味 品味 体味——剑锋散文诗集《剑煮红颜》读后感
腊梅报春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 看得见文脉 望得见山水
晏殊最经典的10首宋词,语言美,意境美,每一首都值得背诵
生命的流响——徐华亮《野岸集》新书首发暨有声语言艺术分享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