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勒贝克:继加缪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两部作品:《血清素》《反抗世界,反抗人生》。尽管维勒贝克凭借《地图与疆域》斩获法国文学最高奖项龚古尔文学奖,被誉为“继加缪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但中文世界的读者显然对他不够了解——至少不像对加缪那样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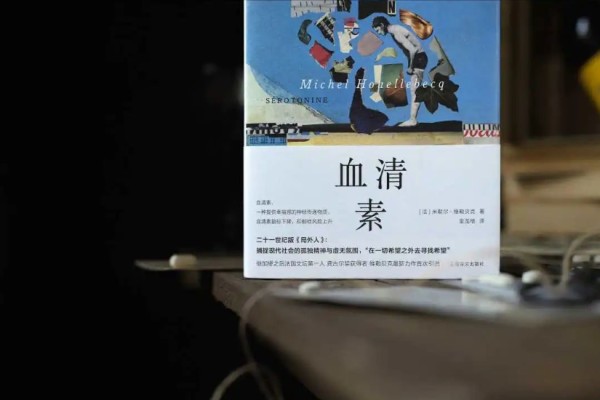
《血清素》[法]米歇尔·维勒贝克 著;金龙格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1世纪版《局外人》:捕捉现代社会的孤独与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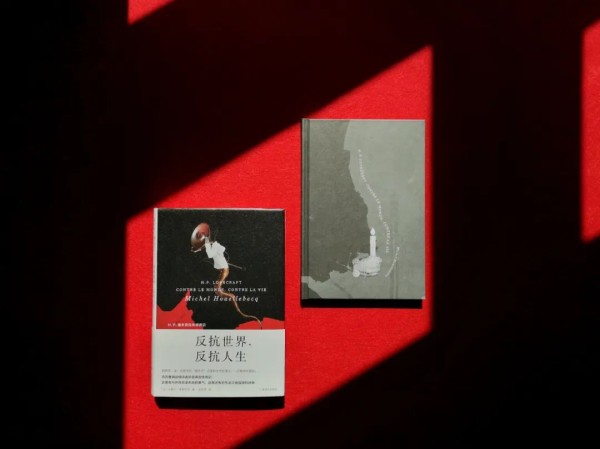
《反抗世界,反抗人生》[法]米歇尔·维勒贝克 著;金桔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克苏鲁神话缔造者的非典型性传记
本文来自《巴黎评论》的一篇访谈文章,在一种略显轻松随意的谈话氛围中,一起了解这位享誉世界的法国作家,也能从中看出,维勒贝克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物,他松散、浪漫,常常语出惊人。
本篇访谈译者:丁骏
访谈出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马鸣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2019年5月出版。
“你喜欢‘傀儡乐队’吗?”采访第二日,米歇尔·维勒贝克这样问我。他放下手中的电子烟(他每吸一口,电子烟就会发出红光,产生水汽,而不是烟),慢慢从他的蒲团沙发上站起来。“伊基·波普根据我的小说《一个岛的可能性》写了几首歌,”他说道,“他跟我说那是过去十年里他唯一爱读的一本书。”这位法国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打开他的苹果手提电脑,小小的厨房间里顿时充满了那个已经成为朋克传奇的沙哑声音,它在唱着:“死了也挺好。”
米歇尔·维勒贝克一九五八年出生在法属留尼旺岛,靠近马达加斯加岛。如他的官方网页所言,他的波西米亚父母,一位麻醉学家和一个登山导游,“很快对他的存在不再感到任何兴趣”。他没有一张自己童年时的照片。最初他在阿尔及利亚与外祖父母住了一段时间,从六岁开始他在法国北部生活,由他的祖母抚养成人。维勒贝克过了一段没有工作、被抑郁症所困的生活,几度进出精神病院,之后他在法国国民议会里找了份做技术支持的活。(国会成员们“非常友好”,他这么说。)
维勒贝克在大学时就是个诗人。一九九一年他写了一本研究美国科幻小说作家H.P.洛夫克拉夫特的书,深受好评。三十六岁那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战线的延伸》(1994),讲两个电脑程序员的无聊人生。这部小说吸引了一小批狂热追捧者,还有一队粉丝受书的启发办了一份杂志,名为《直立者》,基于一个他们称之为“抑郁主义”的运动。(维勒贝克接受了名字登上刊头的荣誉,他说自己“并不真地明白他们的理论,而且,坦白说,也不在乎”。)他的第二部小说《基本粒子》(1998)混合了社会评论和直白的性描写,这部作品在法国卖了三十万册,令他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激烈争论,关于维勒贝克到底是个秉承巴尔扎克之伟大传统的了不起的现实主义大师,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虚无主义者。(一位一头雾水的《纽约时报》评论家将小说描述为“令人深深作呕”。另一位形容该书“在淫秽色情和精神错乱之间郁郁蹒跚”。)《直立者》的编辑们深受冒犯,认为这本书是维勒贝克对性解放运动的反动谴责,于是把他踢出了杂志。
几年之后,他的母亲出版了一本四百页长的回忆录,她感觉在《基本粒子》中有一些自传性质的部分,对她的描述很不公平。维勒贝克在他的公众生活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获得了法国媒体的普遍同情,人们不得不承认,与这本自传中那个唯我独尊的女人比起来,《基本粒子》中对那位嬉皮母亲的苛刻描述简直可以算客气的。在她的巡回售书活动上,她问了一句很出名的话:“有谁没骂过自己的儿子是个可怜的小蠢货呢?”
维勒贝克素来有醉酒和向采访他的女人献殷勤的名声,所以我按响他在巴黎的短租小公寓的门铃时,心情略微有点忐忑。但是我们一起度过的两天中,他礼貌周全,还有些害羞。他身着一件旧的法兰绒衬衣,脚上穿着拖鞋,他的慢性湿疹显然正处于发作期。采访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坐在那个蒲团上,抽着烟。(他想从一天四包的量减下来,所以才会有电子烟。)我们说法语,偶尔才用英语,维勒贝克的英语听力没问题。我的每个问题一出口,都是一段葬礼般的寂静,他总是吐着烟,闭著眼睛。我不止一次心想他该不会已经睡着了吧。最终,他会给出答案,以一种精疲力竭的单一音调,直到第二天他的声音才略微有了点精神。他后来发来的邮件也都是兴之所至,让人着迷。
维勒贝克目前单身,曾两次离婚,第一次婚姻有一个儿子。从二○○○年起他住在爱尔兰的西海岸,夏天在安达卢西亚的公寓度过。
——苏珊娜·哈尼维尔,二○一○年
农民,码农,作家
《巴黎评论》:谁是您的文学前辈?
米歇尔·维勒贝克:最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一直都是波德莱尔曾经非常震撼我,还有尼采和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还有巴尔扎克。这都是真的。这些是我崇拜的人。我也喜欢另外一些浪漫主义诗人,雨果、维尼、缪塞、奈瓦尔、魏尔兰以及马拉美,既因为他们作品的美,也因为这种美所富有的骇人的情感张力。但是我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童年时念过的书对我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
《巴黎评论》:比如说呢?
维勒贝克:在法国有两位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家,儒勒·凡尔纳和大仲马。我一直更喜欢凡尔纳。而大仲马的作品太多历史的东西,让我感到无聊。儒勒·凡尔纳对这个世界有种海纳百川的视角,深得我心。世上任何东西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故事对我的影响也很深。这些故事让我难过。
我读波德莱尔出奇得早,大概才十三岁,但撼动我生命的人是帕斯卡尔。那年我十五岁。我们全班去德国旅行,是我第一次出国,很奇怪,我带的书就是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我被下面这段话吓到了:“想象这样一群人,他们带着镣铐,全都被判了死刑,每天都会有几个人当着所有其他人的面被杀死;那些还活着的人在同伴身上看到自身的处境,互相伤心而又绝望地注视着,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刻。这便是人类处境的写照。”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因为我是由我的祖父母带大的。我突然意识到他们会死,而且可能很快就会死。我就是那时候发现了死亡。
《巴黎评论》:还有哪些作者对您产生过影响?
维勒贝克:我读了很多科幻小说。H.P.洛夫克拉夫特和克里福德·西马克。《城市》是部杰作。还有西里尔·科恩布鲁斯和R.A.拉弗蒂。
《巴黎评论》:是什么让科幻小说如此吸引您?
维勒贝克:我觉得有时候我需要摆脱现实。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觉得我是个现实主义者,还会略作夸张。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的呼唤》有一点肯定对我有影响:他使用不同的视角。先是一段日记,然后是一个科学家的日志,跟着是本地一位白痴的证词。你能在《基本粒子》中看到那种影响,我从关于动物生物学的讨论到现实主义,再到社会学。如果不算科幻小说,给我最大影响的作品就都属于十九世纪了。
《巴黎评论》:您有一点科学背景。高中毕业后,您学了农艺学。什么是农艺学?
维勒贝克:所有跟食物生产有关的东西。我做的一个小项目是绘制科西嘉的植被地图,目的是找到能放羊的地方。我在学校手册上读到学农艺学以后可以从事各种工作,但后来发现这种说法很可笑。大多数人就是干某种务农的活,只有少数几个挺有意思的例外。比如我有两个同学成了牧师。
《巴黎评论》:您学得开心吗?
维勒贝克:非常开心。事实上,我差点成了科研者。那是《基本粒子》中最具自传性质的内容之一。我有可能做的工作是找到一些数学模型,可以用于罗讷-阿尔卑斯地区楠蒂阿湖的渔民人口。但奇怪的是,我拒绝了这份工作,这是很傻的,事实上,因为我后来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巴黎评论》:最后您做了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这之前您有类似经历吗?
维勒贝克: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那时候对程序设计需求特别大,而且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专科学校,所以很容易进去。但我立即就对这份工作深恶痛绝。
婚姻是为了对抗孤独的生活
《巴黎评论》:您的第一本小说《战线的延伸》关于一个计算机程序员和他的性压抑的朋友,是什么促使您写这部小说的?
维勒贝克:我从没见过哪本小说声明进入职场如同进入坟墓。自此之后再也不会发生什么,而你还得装出一副对工作感兴趣的样子。此外,有些人会有性生活,而另一些人没有,仅仅因为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有吸引力。我想指出如果有人不过性生活,那不是出于道德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长得丑。你一旦把这话说出来,感觉显而易见,但我就是想把这话说出来。
《巴黎评论》:可怜的提泽朗没人喜欢,他是个非常深刻的人物。
维勒贝克:他是个不错的人物。回过头去看看,我自己都奇怪,仅仅靠着性压抑这一块跳板,竟然就弄出了一个这么有趣的人物。提泽朗这个人物的成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
《巴黎评论》:据《战线的延伸》里的叙述者说,“年轻遭人恨”。
维勒贝克:那是陷阱的另一部分。第一部分是职业生涯的现实,不会再发生任何事情。第二部分就是会有一个取代你的人,各种经历都是属于他的。这就引出父亲对儿子的天然憎恨。
《巴黎评论》: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维勒贝克:是的。女人怀孕时会经历某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那是动物生物学。但父亲们对自己的后代完全不当回事。会有荷尔蒙一类的事情发生,对此任何文化都一筹莫展,一般来说女人会喜欢孩子,而男人则基本上不把它们当回事。
《巴黎评论》:那婚姻呢?
维勒贝克: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会在大学里遇到很多人,而一旦进入职场,他们基本上就不会再遇到谁了,这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生活变得无聊,所以人们就结婚,过自己的生活。我可以说得更具体些,但我想谁都明白。
《巴黎评论》:所以婚姻只是对抗……
维勒贝克:对抗一种相当孤独的生活。
《巴黎评论》:您一度找不到出版社愿意接受《战线的延伸》。编辑们为什么拒绝这本书?
维勒贝克:我怎么知道。不过这本书看起来与当时出版的任何书都不一样。比如,那时候勒克莱齐奥被认为是个伟大的作家,我想。
《巴黎评论》:您现在怎么看您的第一部小说?
维勒贝克:这本书很野蛮,但是本好书。我是从那时开始和Les Inrockuptibles长期合作的,他们一看就喜欢上了这本书。
《巴黎评论》:Les Inrockuptibles?
维勒贝克:这是一份杂志,大概三分之一音乐,三分之一文学,还有三分之一什么都有。杂志刚开办的时候[一九八六年做月刊,然后一九九五年起做周刊]法国媒体被吓坏了,因为它胜过市面上所有其他东西。传统周刊还有它们的文学副刊与之相比都显得可笑。巴黎知识分子圈里所有算得上的人物都拜倒在他们脚下。不幸的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责任感,所以也就没有人真正负责。如今杂志已经完了。
《巴黎评论》:一开始有哪些价值观?
维勒贝克:你可以说只有一个——来点现实,老兄!让我们看看真实的世界,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植根于人们真实生命中的事情。
“展示价值观自由化所造成的灾难”
《巴黎评论》:一九九八年,您出版了第二本小说,如今闻名遐迩的《基本粒子》,讲一位杰出科学家的悲剧爱情生活和他那位性压抑的同母异父弟弟。是什么让您写这本小说的?
维勒贝克:真正的灵感是一九八二年的阿兰·阿斯佩克特实验。这些实验展示了EPR悖论:粒子一旦互相起反应,它们的命运便互为连结了。当你作用于一个粒子,其效应立即传递到另一个粒子,即便它们相距遥远。这真的让我震撼,两个事物一旦发生连结,就会永远连结。这标志着一个哲学上的基本转折。自从宗教信仰消失之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称我们孤独无依,并把人性归结为生物学现象。人就和台球一样可以被计算,面对的是彻底的腐朽毁灭。这种世界观受到了EPR悖论的冲击。所以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一个设想,设想下一个形而上的变异将是什么样的。它肯定不会比唯物主义更让人沮丧。唯物主义是很让人沮丧的,这我们得承认。
《巴黎评论》:您是怎么从这个设想发展出一个故事的?
维勒贝克:我从主要人物迈克尔开始,他是个物理学研究者。接着,就是布鲁诺,他是提泽朗的延续,因为我在《战线的延伸》里杀死了提泽朗,至今都感到遗憾。这一次我要写写他的生命故事。那是真正的愉悦。写迈克尔不如写布鲁诺好玩,因为我得读很多书。
《巴黎评论》:您得做大量量子理论的研究。
维勒贝克:哦,真是可怕。我记得有些书难到同一页我得读上三遍。有时候在智力上做些努力也挺好,但是我怀疑自己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巴黎评论》:他们说您在政治上是右派,因为在《基本粒子》中您似乎反对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您对这种分析怎么看?
维勒贝克:我的想法基本上就是,对于重大的社会变化你是不可能做什么的。家庭单位正在消失,这也许很可惜。你可以争辩说这会增加人类的痛苦。但是可惜也好,不可惜也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是我和反动派之间的区别。我对于拨回时钟完全没有兴趣,因为我不相信我们能做到。你能做的只是观察和描述。我一直喜欢巴尔扎克的一句很侮辱人的话,他说小说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由价值观变化所造成的灾难。他夸张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在展示价值观自由化所造成的灾难。
《巴黎评论》:您曾写过您“不仅是个宗教上的无神论者,也是个政治上的无神论者”。您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儿吗?
维勒贝克:我不太相信政治对历史的影响。我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科技,有时候,不常常是,也有宗教因素。我不认为政治家们真的能有什么历史的重要性,除非他们造成重大的拿破仑式的灾难,但至多到那个程度。我也不相信个体的心理对社会运动有任何影响。你会在我所有的小说中找到这个观点。今天早晨我和人讨论比利时,一个完全不对劲的国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没人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比利时人自己似乎很愿意、很想让国家对劲起来。但还是不行。这个国家就要消失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存在一些巨大的社会力量,那是用个体心理学无法解释的。
《巴黎评论》:《基本粒子》一书获得的反响让您吃惊吗?
维勒贝克:是的。我期待它能有我第一本书差不多的成功。获得评论家的肯定,有一定的销售量。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因为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巴黎评论》:从《基本粒子》开始您会玩世不恭地利用媒体给每本书做宣传,您的法国评论家们对此很有意见。那时候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维勒贝克:那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想卖书就得大量上媒体曝光,我确实想赚钱,这样可以辞掉工作,这也是真的。那是有钱的唯一作用,换取自由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没那么肯定媒体能卖书了。
《巴黎评论》:那什么能卖书?
维勒贝克:口口相传。比如,眼下法国最畅销的作家是马克·李维。他从来不上媒体。
《巴黎评论》:评论家们也是因为《基本粒子》开始关注您的生平,因为书中人物似乎跟您有很多共同点。但你似乎对此很厌烦,即人们总把一切归结为传记。
维勒贝克:是的,很烦人,因为这否定了小说写作的一个核心特点,即人物们是自发生长的。换句话说,你从一些真实的事实出发,然后你就任由它凭着自己的动量滚动向前。你走得越远,就越可能把现实完全抛到身后。事实上你是没法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你可以使用其中的元素——但别以为你能控制一百页之后某个人物会做出什么事来。你唯一能做的是,比如,赋予这个角色你自己的文学品位。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让他打开一本书就是了。
“青春期从来都不如童年愉快”
《巴黎评论》:说到您的生平,您最近写过您有一个和祖母一起度过的幸福童年。
维勒贝克:是的,我的祖母。我六岁到十八岁之间和她一起生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真正的幸福,六岁到十二岁之间。我们住在约纳的乡下。我骑自行车。我搭建水坝。我读了很多书。没有太多电视。这很好。但是后来我们搬去了克雷西-布里。如果你现在去那里,不太能找到当时的感觉。那时候更农村。现在基本上都是郊区项目。但我还是感觉不舒服。人太多了。我喜欢乡下的荒僻。
但是,说实话,青春期从来都不如童年愉快。
《巴黎评论》:六岁之前您和您的外祖父母住在阿尔及利亚。您还记得您儿时的事吗?
维勒贝克:非常少了。我模模糊糊记得有操场,上面有很多树叶。我也记得催泪瓦斯的味道,我很喜欢。我记得关于战争的一些小事,比如大街上开机枪。
《巴黎评论》:那吓人吗?
维勒贝克:不,一点儿也不。孩子们会觉得那些事情很好玩。
《巴黎评论》:您小时候家里人都读书很多吗?
维勒贝克:我的祖父母完全不读书。他们不是受过教育的人。
《巴黎评论》:那么《基本粒子》之后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维勒贝克:《基本粒子》最重大的影响除了钱和不用工作之外,就是我有了国际名声。比如,我不再做游客了,因为我的巡回售书活动满足了我可能有的旅行欲望。于是我也访问了一些一般人不太会去的国家,比如德国。
《巴黎评论》:您为什么那么说?
维勒贝克:没有人会在德国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在那里不存在。但是他们那样做是错的。没有那么糟糕。
“我从来不计划任何东西”
《巴黎评论》:您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维勒贝克:这很难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得写作文,比如“描述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写这些小文章时感到的快乐确实有些不成比例,而且我会把文章留着。此外,我还写日记,尽管我不确定那时候我能写点儿什么。我觉得我更可能描写自己做的梦而不是日常生活。
《巴黎评论》:您现在的写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维勒贝克:我大概凌晨一点醒过来。我在半清醒状态中写作。等我喝了咖啡,我会越来越清醒。然后我就一直写一直写直到写得烦了。
《巴黎评论》:您写作时还有别的要求吗?
维勒贝克:福楼拜说你得永远处于勃起状态。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得时不时地散个步。其他方面嘛,饮食的话,有咖啡就行,真的是这样。咖啡会带你经历不同的清醒阶段。你一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你写啊写。你喝更多的咖啡,你的清醒程度增加,这样的中间状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这种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
《巴黎评论》:您会给小说设计情节吗?
维勒贝克:不会。
《巴黎评论》:您不知道从这一页到下一页会发生什么?
维勒贝克:我从来不计划任何东西。
《巴黎评论》:那您的风格呢?您有一个习惯,您会做一些野蛮的、常常是有趣的并置,比如“我儿子自杀的那天,我做了一个番茄煎蛋饼”。
维勒贝克:我不会真的把那个说成风格。那只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我身上存在一种紧张,会让我不假思索地写出并置句。那和朋克摇滚没有太大区别。你尖叫,但是你也略作调整。有关于我的风格的渐进研究。
《巴黎评论》:有什么结论吗?
维勒贝克:我的句子长度中等,有丰富的停顿。换句话说,我的句子属于中号,但是有各种切割法。副词是人们厌恨的一样东西。我用副词。还有一个东西源于我是诗人的事实。文字编辑总是要你去掉重复。我喜欢重复。重复是诗歌的一部分。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重复我自己。事实上,我觉得我是今天还在写作的作家中最爱重复的一个。
《巴黎评论》:您喜欢引用商品名字。比如,“loupau cerfeuil Monoprix Gourmet”[“不二价美味海鲈配西叶芹”]。
维勒贝克:“海鲈配西叶芹……”很诱人。写得好。我使用商品名字也因为它们,客观来说,是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倾向于选择名字最诱人的商品。比如这个词“西叶芹”很有吸引力,尽管我根本不知道西叶芹是什么。你想吃点带西叶芹的东西。这很美。
《巴黎评论》:您写过灵感的源头之一在于人们会跟您讲他们生活中的故事。显然,陌生人喜欢向您袒露内心。
维勒贝克: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精神科医生,因为我能给人不偏不倚的印象。事实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我对于自己听到的事情非常震惊。我只是不表现出来。
唯物主义和爱情不太合拍
《巴黎评论》:您对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的可能性怎么看?
维勒贝克:要我说,爱情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我的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就和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是一样的。
《巴黎评论》:爱情也许已经不存在了?
维勒贝克:这是当下的问题。
《巴黎评论》: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爱情的消失?
维勒贝克: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我们是孤独无依的,我们孤独地活着,然后我们孤独地死去。这一观点跟爱是不太合拍的。
《巴黎评论》:您有侮辱人的特殊天分。您侮辱别人会很开心吗?
维勒贝克:是的。我不得不说,能获得满足感。
《巴黎评论》:您说过您在《一个岛的可能性》的最后部分让诗歌在一部小说中获得胜利,对此您很骄傲。那个部分是讲克隆人没有获得允许便离开了限制区,他要在岛上游荡,去寻找另一个克隆人。
维勒贝克:我个人很喜欢《一个岛的可能性》的最后部分。我觉得它跟我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但没有哪个评论家提到这一点。很难解释,但我有种感觉,最后这部分有一些非常非常美的东西。他打开门,那是另一个世界。我写那一段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故事,我完全陶醉于自己的语言之美。
我做了一些特别的事,为那个最后部分做准备。我停止了写作。有两个星期,我什么也没做——我是说真的什么也不做。我谁也不见。我不跟任何人说话。原则上来说,你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不应该停下来。如果你停下来去做别的事情,那是灾难。但是这一次,我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就为了让写的欲望生长。
《巴黎评论》:您说过自己是“躁郁症患者”。那是什么意思?
维勒贝克:那意思是你往返于抑郁和兴奋之间。但话说回来,我怀疑自己不是真的抑郁者。
《巴黎评论》:那您是什么呢?
维勒贝克:就是不怎么活跃。事实是,我如果上床什么也不干,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会很满足。所以那不是你真正会叫作抑郁的东西。
《巴黎评论》:那是什么阻止了您屈从于您以前说过的最大的危险呢?也就是躲在角落里闷闷不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全都糟糕透了。
维勒贝克:眼下我希望被爱的渴望足以驱使我行动起来。我希望有人爱我,尽管我有缺点。说我是教唆者不太准确。一个真正的教唆者说一些不经思考的话,只为惊世骇俗的效果。我试图说经过自己思考的话。当我感觉到我思考的东西将会让人不愉快,我就会带着真正的热情迫不及待地说出来。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希望被爱。当然,这能维持多久,完全无法保证。
《巴黎评论》:您为什么不住在法国?
维勒贝克:部分是为了少交点税,部分是为了学习你们的美丽语言。也因为爱尔兰非常美,尤其是西部。
《巴黎评论》:不是为了逃避您自己的国家?
维勒贝克:不是的。我走的时候带着荣耀的光环,没一个敌人。
《巴黎评论》:那您怎么看这个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世界?
维勒贝克: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发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有私人公司为送信、收垃圾这样的事情互相竞争。这里报纸上的金融版要比法国报纸里的厚多了。
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男人和女人更加分立。比如你去一个饭店,你常常看到女人们一起吃饭。而法国人从那个角度来看相当拉丁化。人们觉得全是同一性别的人吃晚饭会很无聊。在一个爱尔兰的宾馆里,我看到一群男人边吃早饭边聊高尔夫球。他们走了之后一队女人坐下来,讨论其他的话题。仿佛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物种,然后偶尔为了生育碰个头。
《巴黎评论》:您说过您身上可能有美国人的一面。您的证据在哪里?
维勒贝克:我几乎没有证据。有一个事实是,如果我住在美国,我想我会选雷克萨斯的车,那是性价比最高的。更玄乎的是,我有一条狗,我知道那是在美国很流行的一个品种,威尔士柯基犬。有一样我肯定是没有的,就是美国人对大胸的痴迷。我必须承认,对大胸我没感觉。但是能放两辆车的车库?我想要一个。带那种制冰器的冰箱?我也想来一个。美国人喜欢的我也喜欢。
本文仅代表转载平台和作者本人观点。
经公众号“上海译文”(ID:stphbooks)授权转载。原文及标题略有改动。
图片来源于上海译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网址:维勒贝克:继加缪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 https://mxgxt.com/news/view/1049117
相关内容
维勒贝克:继加缪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塞缪尔·杰克逊合作拍档
求法兰克王国墨洛温及克洛维王朝家族谱系!
牵手“长跑之王”贝克勒,安踏开启非洲“高原C计划”
【塞缪尔·杰克逊】美国影视演员
阿凡达女郎新作预告 佐伊成吕克·贝松新缪斯
泰勒·斯威夫特与运动明星交往,作为过来人贝克汉姆有话要说
最受欢迎的几位法国男明星!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书信里的禁忌恋情:加缪和情人玛丽亚·卡萨雷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