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最初士人是社会阶层的概念,文人和它之间有何差别?
嵇书绝交:文人与士人的分化。士人,最初是社会阶层的概念,开始用以指代贵族的最低层次,后来下移为四民之首。汉代以来,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开始,士人由先秦的游士转型为儒士,而东汉又演变为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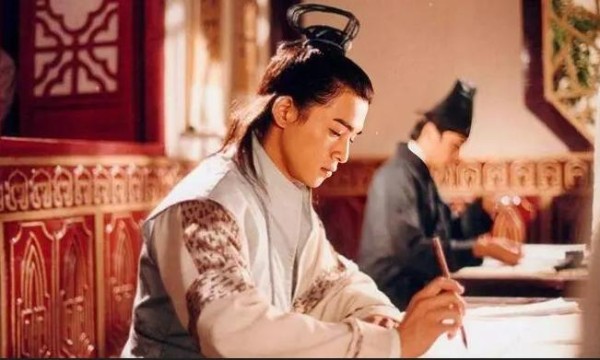
无论他们是游士还是儒士,无论他们属于贵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是受过教育的,都是有或曾经有过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
这与他们的身份和受过的教育息息相关:在身份上,他们是连接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纽带,生活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衣食无忧又受过教育的他们如果想提高社会地位,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在教育上,汉武帝以来,士人受到的正统教育就是儒家教育。
儒家思想对“礼”的重视,就是对社会秩序的重视;而对“仁”的重视,就是对社会群体的重视;君子“终日乾乾”,提倡的是刚健有为;儒家的义利之辨,指明的是道德准则。在这样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下,士人自然会拥有社会理想,怀抱用世之志,将之视作人生的首要目标。
文人同样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会将参与社会政治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出仕与归隐之间,他们的选择会相对更加自由。马良怀先生对文人与士人之异同有如下论述:
文人和士人有联系,因为他们同属于知识阶层;但是文人不是去讲安邦治国的那些大道理,不是讲经世致用这些东西,而主要是言志抒情这一类,抒发自己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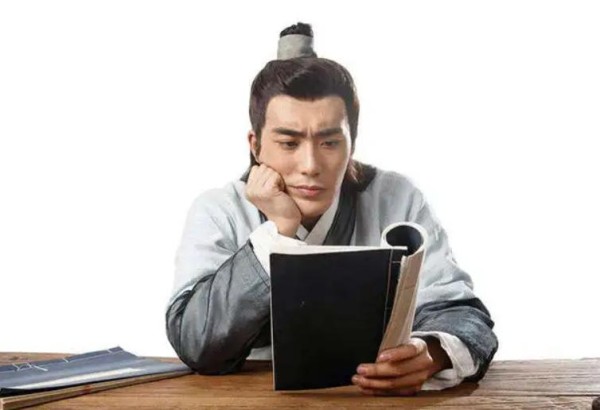
文人和士人确如马良怀先生所说,同属于知识阶层,但是文人本身就是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心中不可能没有士人的志向,只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任何人的选择空间都是很小的,文人由于相对衣食无忧,可以有是否为官两种选择。
因此,文人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因主观或客观原因不能在功业上有所作为的士人。一言以蔽之,文人之所以从士人中分化出来,还是因为在可以选择不做官的情况下,做出了不走仕途的选择。在司马昭执政时期,竹林七贤是文士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缩影。在他们身上,就完整体现了隐与仕两种选择。
嵇康是主动选择不走仕途的标志性人物。他与魏宗室长乐亭主通婚,曾“拜中散大夫”,似乎是个闲职。他不同于出仕为官的哥哥嵇喜,为人恬静寡欲,志不在此,后来司马氏掌权,他更加没有做官的欲望,也懒与人共,交游甚少。
即使在“竹林七贤”中,嵇康真正的神交之人也只有阮籍和山涛,其余四人不过是豫附者。就是这样的交情,也不能左右嵇康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当山涛推举嵇康为官时,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来申明自己的思想与抉择。
然而空言不了解难以让人信服,嵇康紧接着就用“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两句相反的描述来概括山涛与自己的性格:您是个通达的人,经常是肯定而很少猜忌责备;而我性情耿直,心胸狭隘,很多事情难以容忍,这样就把自己和山涛拉到了对立面上。

可是山涛与自己毕竟是知交好友,非同一般,自己又不是容人的人,那要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其实嵇康写到这里似乎也无可奈何,只好以“偶与足下相知”一笔带过来搪塞。
随即马上摆明立场:“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一个“惕”字,既有“敬”又有“怕”的意思,嵇康用在此处,可有两种解释,避免了小人借此生事,又能让山涛明白他对官场的印象。仕途升迁在旁人眼中都是可喜可贺的好事,但我嵇康就是不喜欢这个,非但不喜欢,反而惧怕,又怎能因为你的升迁而高兴呢?
那我惧怕的又是什么呢?嵇康反其道而用“越俎代庖”之典,这里没有说祝者去代厨师割肉,而是厨师拉祝者操刀,一个“羞”字虽不着痕迹,但已然说明了山涛此举并非好事:庖厨之人因为割肉腥膻而以为羞耻,就拉祝者与他一起,山涛荐他做司马氏的官,其行为无异于拉人割肉。
割肉一事极易令人联想到司马氏对天下名士的血腥屠戮和弑君之行,山涛为司马氏服务,在嵇康眼里看来与割肉的厨子没什么两样。此话一出,既讥刺了司马氏的行为,又讽刺了山涛所为,字字诛心,有一石二鸟之效。以上是这封信的首段,嵇康通过对比与反向用典来与山涛划清了界线。

历来分析嵇康此文者,多以其“不堪”“不可”为重,然《晋书》于此信之首段便做了极大的删节,仅存如下两句,我们不可不察: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两相对照之下,其巨大差异显而易见:若仅观这两句,我们不仅绝难看清嵇康此前与山涛的知交情谊,更难体会他划清界线的鲜明与表明立场的急切。而且单就反向用典而言,“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不仅活灵活现,而且语意峻切,删去以后,整个语气就和缓了许多。
且末句一个“具”字饱含决绝陈词之意,删之则此意全无。史家于此显然不是无心所为,这就更加反映出嵇康此书首段在全文中的位置之重,亦可知嵇康之文的巨大影响。

嵇康在反向用典辛辣讽刺过后,没有接着疾言厉色,而是先夸了山涛一句,说自己曾在书上见过既能兼济天下又能耿介自守的人,有人说这种人不存在,他现在才相信这种人真实存在,意指山涛即是这种人。
然后又开始表明立场——虽然你是这种难得的人,但我不是:我就是这个性,对某些人和事就是不能忍,实在不能勉强。随即话锋一转:现在大家空言有一种通达的人,他们没有不能包容的,外在跟世俗的人没有差别,而内心却仍坚持正道,能够与世随波逐流而不觉得忧虑。
这里嵇康虽未刻意强调“空语”二字,但也不难看出,他对这种人的描述是开头对山涛描述的具体化。也就是说,他不着痕迹地否定了自己“信其真有”的话——能在官场中随波逐流且坚持本心,是空谈!
紧接着嵇康便一连列举了11位历史人物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老子和庄周,是他要引以为师的;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是他不敢小看的;孔子兼爱,执鞭赶车也不会羞愧,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用世济民的心意,也就是所谓显达时能够兼济天下而不改己志,困窘时能够安然自若。

这样看来,许由在尧舜的治世隐居山林,张良辅佐汉朝,接舆凤歌笑孔,他们都一样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君子的各种行为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顺着本性行事,各得心安之所。
嵇康的这些列举,虽在表面上说没有区别,但是他明确对老子、庄周表明了推崇,对柳下惠、东方朔进行了肯定,而对孔子和子文,他未置可否,只是看似客观地说这是“君子思济物之意”。细细究之,我们便知:孔子不以执鞭为耻,是在“富而可求”的情况下,对子文的行为,孔子的评价是“忠”。
那么嵇康之意就显而易见:孔子、子文这些人的选择,在他看来是世俗的,是不被他肯定的。可他又说这些人都是“循性而动”,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在嵇康眼中,虽然“循性而动”没有差别,但士人之“性”却各有不同,许由在尧舜之世尚且不与朝廷合作,在司马氏的统治下还在朝为官,心性又是如何?
这一段的最后,嵇康表示“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来继续表明他的心志,这里的“志气”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儒家于男子而言,讲的是“匹夫不可以夺志”,女子改嫁,也会以“夺志”来作为婉辞。嵇康做如此说,更加令人难以回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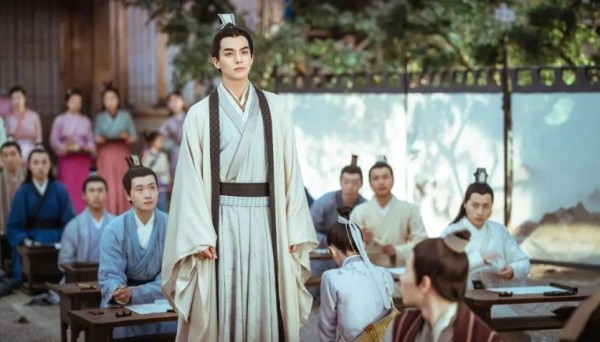
读了《庄子》《老子》后,自己的行为加倍放旷,所以追求仕进荣华的想法日益减弱,而任诞率真的情性则越发浓厚。随后并没有详细解释自己如何“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只是以野兽是否能够驯化作比:如果从小就被驯化养育,就会服从主人管束;
结语
如若长成才去束缚,就会疯狂地摇头跺脚以求挣脱羁绊,甚至是赴汤蹈火也毫不在意,即使勒的是金笼头,喂的是最好的饲料,还是会强烈思念它的密林和青草,说明自己习性已然养成,一旦被约束就会不顾一切以至疯狂,即便是在约束下受到最好的待遇,他也依旧不以为然,心里还是向往自由。
网址:魏晋时期,最初士人是社会阶层的概念,文人和它之间有何差别? https://mxgxt.com/news/view/949398
相关内容
明星与豪门:香港社会阶层差...@穿梭时空的路人的动态《张医生与王医生》:两个工人子弟的阶层跃升与社会变迁
“阳刚之气”的理想与现实: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男人是如何理解男子气概的?
穷人与富人的不同选择:从深度剖析嫖娼行为看社会阶层差异
一文说透有上、中、下社会阶层的区别,这就是我要远离底层的理由
明星属于什么社会阶层?
浙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寻美兰溪·重返芥子园”
概念分析初探
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顾农:闲谈魏晋风度与文学——人民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