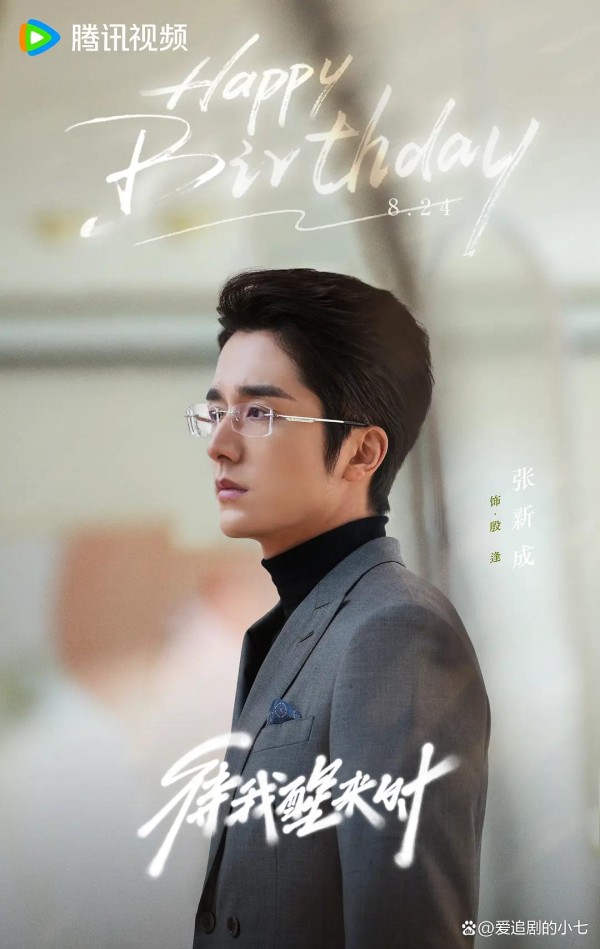浅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上天降下的灾异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与“天”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司马迁极为关注的问题。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目的,对于其真实内涵,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往学者多从探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理解,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纵观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发现,“天人之际”的内涵似乎又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关联、互相制约的角度来理解“天人之际”,这个命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包括司马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就是“天人”关系问题。我们在此探究的司马迁的“天人之际”,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的。此外,历史已经证明,灾异发生之时,也是古人心目中天人矛盾集中爆发之时,因而,天人关系往往集中反映在人事与灾异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概念问题。
《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集中阐发了自己对“天人之际”问题的思考,这篇文献也成为我们探究司马迁天人思想最主要的史料依据。然而,在研读《天官书》时,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该篇的正文部分与论赞部分在思想旨趣上并不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这就造成了研究上的诸多困惑,也正是基于此,学者在对司马迁天人关系问题上的研究也呈现出很大的分歧与差异。司马迁对待灾异及天人之际问题的态度到底如何呢?对《天官书》正文部分与论赞部分的思想龃龉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

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似乎不应该这样自相矛盾。这从逻辑上肯定是说不通的。《天官书》的论赞部分显然是司马迁本人的思想,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天官书》的正文部分会不会只是一种记录,而并不代表他本人的思想观点呢?要厘清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讲,首先要搞清楚司马迁撰写《天官书》的目的是什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谈到了这个问题。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司马迁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神秘之文,是荒诞不经的东西。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录入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中谈到“阴阳之术”时,司马谈为其下的评语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重视吉凶祸福的预兆,讲究的禁忌避讳特别多,让人受到很大的拘束,整天都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这显然是否定性的评价。
司马谈认为,“未必然也”。司马迁继承了其父的思想衣钵,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更是直接批评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宏大不经”,并对“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的“浊世之政”进行了抨击。可见,司马迁对充满禨祥神秘之气的星气、星占等荒诞不经的东西是持一贯的否定态度的。这是司马迁对星气之书的总评价,是这段话的第一层意思。“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星占家用这些星气之书来占验人间祸福,往往言之凿凿,屡试不爽。这说明星气之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这是第二层意思。

“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对于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的星占之书,采用回避的态度是不行的,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些星占之辞一一罗列出来,再用天体运行的规律——“轨度”来加以检验,这才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正确态度。这里,司马迁对《天官书》的整体结构已经做了安排,“首先把‘多杂禨祥,不经’的星气之书原貌展示给后人,以使后人知道当时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思想氛围之中,然后再正面阐述自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并用天体运行的规律去验证星气之书和星占家们占辞的荒谬。”这是第三层意思。
事实上,司马迁也的确是这样安排这篇文章的结构的。《天官书》正文部分首先讲述了中宫天极、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等五部列宿的分布情况及各种象征意义,日、月和岁(木)、太白(金)、荧惑(火)、填(土)、辰(水)五行星的运行情况,以及一些重要星体的方位、形态及相关预兆等。然后,正文部分进入第二个大问题——望气之术,二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星气之书了。这些内容,是否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多杂禨祥,不经”的星气之书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天官书》正文每一个条目之后,都是某星主某事,某气主某事,某现象主某事这样的禨祥之辞。按照这样的说法,人们面临的一切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大到自然灾害的发生、国君的荣辱祸福、战争的胜负,小到谷物的收成甚至鱼盐贵贱,都有“星气”的前兆,都可在星气之术中找到确凿的证据!冥冥之中,天上的星空决定了人间的一切祸福喜乐,人如同一颗棋子,被“星气”——上天——这只主宰一切的大手操纵着。这是彻头彻尾的宿命论和禨祥迷信思想。若据此,司马迁简直就成了星气之术及天人感应说的狂热鼓吹者。我们认为,这些内容不可能是司马迁的天人之际思想。这里试举几例来看。

首先,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是一位优秀的天文学家,他曾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太初历》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推算出了日蚀的周期性规律,自从有了这个周期规律,人们就可以据此矫正朔望,过去人们眼中可怕的灾异——“日食”,似乎也就不再像原来那样是令人恐惧的“天变”了。如此,《天官书》正文部分出现的“日蚀,国君”云云,显然就是“不经”之谈了。司马迁在理性上估计也不会大肆宣扬这些东西了。
其次,对于国君的强弱祸福,战争的胜负之数,司马迁显然也不认同“不经”的星气之书的解释。他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有德”才是国君强大的保障。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项羽的失败,司马迁认为,项羽之失败是因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这才是根本原因,而不是什么“天之亡我”。可见,司马迁对星占之书中关于战争胜负的观点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看星气之书中所说的“鱼盐贵”问题,司马迁是一位颇具经济头脑的历史学家,他对物价涨落问题有精准的认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物价的涨落是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物品的供求关系客观决定的,星气之书中讲的“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就纯属可笑的无稽之谈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天官书》正文部分绝不可能代表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司马迁欲探究的“天人之际”,不可能体现在这些“不经”、“荒谬”的星气之书当中。《天官书》正文部分既然不属于司马迁的“创造”,那么这些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天官书》正文部分记有五星反逆行、变色的现象,这和司马迁读过的“史记”是吻合的。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天官书》的正文部分,就应该是司马迁所看到的“史记”,或者说类似“史记”的其他文字记载。那么,“史记”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则材料:“(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掌天时星历,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这些事情历来是太史令的工作职责,所以,司马迁当上太史令之后所看到的“史记”,应该是历代太史令之类的职官记载的史书及天时星历之书,它们与“石室金匮之书”一样,都属于国家档案。所以,“史记”应是一个泛指的统称,而不是一本具体的书籍。《天官书》的正文部分,就应该是历代太史令所作的天象记录及基于星气之术的注解。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谈到,《史记》中“八书”的作用是“记国家大体。”既然是“记国家大体”,那么《天官书》正文部分记录当时“官方”的正统天人思想及星气之术,也就是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且,从逻辑上讲,司马迁要阐发自己的“天人之际”,首先也应该罗列出当时社会上通行的天人思想,若没有这些东西作参照物,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又如何体现呢?因此,《天官书》正文部分记录的乃是当时通行于世的“官方”星气之书,并不能代表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的真正思考。论赞部分所蕴含的思想才是真正属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一家之言”。

幽王、厉王以来,时间已经很久远了。自古以来所见的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至于“家占物怪”,人们所用的“合时应”的书,“其文图籍禨祥不法”,这样的不经之谈,并不值得人们信任。这段话是司马迁对自古以来星气之书和占验之辞的总体评价。这与《太史公自序》中“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司马迁还认为,孔子从内心里也是不相信这些奇谈怪论的,或至少是保持存疑的态度。
司马迁认为,禨祥星气之说盛行与否,与时代环境是紧密相关的。星占家们还往往依据现行人间秩序,对星象随意解释,前后矛盾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本来二十八星宿主十二州的说法,“所从来久矣”。但秦统一中国后,头顶的星空未变,人间的格局却是旧貌换新颜了。秦本为“夷狄之国”,属阴,太白主之。秦并六国后,一统天下,成为人间格局的主宰者,则应属阳,这时的太白也就不再主“夷狄”,而是主中国了。此时,仍被目为夷狄的胡、貉等游牧民族国家,只好由辰星来“主”了。这样翻来覆去的解释,星占家用一句“更为客主人”就轻轻带过了。对此,司马迁是非常反感的,认为这种随意胡说的东西“无可录者”,毫无价值。
司马迁认为,“为国者”心中必须要有这种宏大的时空观念,经过三大“纪”(4500年)的探索和总结,或许才可以搞清楚“天人之际”的真正内涵。在《天官书》的末尾,司马迁再一次重申了这种思想:“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只有深刻观察,深入思考,辨别真伪,贯通古今,才能对天人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他是相信天人关系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而且规律是需要通过相当漫长的观察和探索才可能掌握的。那么,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具体天象变化,显然并不是人间秩序变化的直接预兆。

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基础上,司马迁对当时流行于世的星气之书和占星之术冠以荒诞“不经”的总体评价。在司马迁看来,天象和人事之间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大谈天人感应和推阴阳灾异的汉儒董仲舒,司马迁还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再如,对于集中阐发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天人三策”,班固《汉书》中一字不漏地予以记录下来。但司马迁在《史记》却一字未提,其思想旨趣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中充满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气息,在当时的思想大环境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人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司马迁的天人思想,“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最高水平。”⑤尽管略有拔高之嫌,但对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整体把握,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太史令,职业的特点加之时代的影响,司马迁自然也难以完全摆脱天人感应及灾异之说。一方面,他对这些东西总体是怀疑的,另一方面,他对这些东西中有的思想成分又是相信的。譬如,司马迁对帝王封禅就是非常赞同的。此外,《史记》中还记载了不少怪诞的故事。这些都体现出了他思想中的矛盾之处。但总体来说,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包含着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清新气息,对天人关系及灾异的理解也是比较理性的。
网址:浅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https://mxgxt.com/news/view/424504
相关内容
讲座|黄德海&刘铮:司马迁是如何成为司马迁的?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汉武帝和司马迁的微妙关系,司马迁对汉武帝的隐晦评价
文史丨太会了!且看司马迁的“追星”往事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除了《史记》本身,还在于他的坚持和隐忍
冯远征自曝是司马迁后裔
李士金中国文化课堂教学改革生态述论——袁编误读司马迁原文以权势名人提携获得知名度
浅谈跨国娱乐企业文化传导渠道研究
浅谈近代城市和女性生活变迁.doc
浅谈娱乐营销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