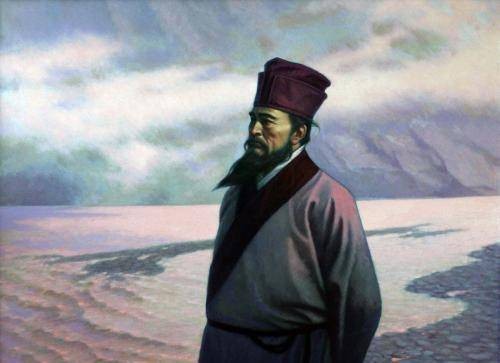EP32|对话彭小波 x 曹梦:SpaceX如何颠覆传统航天?
赛博对话:星舰第十次试飞结果出来后,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彭小波:SpaceX这次试飞的“超重+星舰”,作为一级、二级均能重复使用的重型火箭,我认为它距离最终成功已经非常近了。它和大家熟悉的猎鹰9有个核心区别:猎鹰9是一子级回收,二子级还是传统火箭,入轨送完卫星后会离轨钝化、烧蚀;但“超重+星舰”的考核重点在二级——二级要入轨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公里/秒),再用垂直回收的方式返回地面,这需要复杂的速度控制、气动减速、动力减速,还要应对严苛的热环境挑战。
之前第八、第九次试飞时,星舰就出现过烧蚀问题,尾部六台发动机有点火泄漏的情况。但这次试飞,它成功验证了“平板式第三代卫星”的释放机构——像“发牌机”一样把卫星滑入太空;最终在印度洋的降落也非常可控,结构完整。从宏观判断,技术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距离未来目标不远了。

彭小波:星际荣耀董事长/总经理
赛博对话:星舰的热防护问题,是否有历史教训可参考?
曹梦:其实人类航天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比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就是在载入过程中因隔热瓦故障,热流窜入导致解体。这次星舰第十次试飞,烧蚀问题其实仍很明显,还有防热瓦脱落的情况。但它做了一个关键实验:拆掉了部分关键热流特征点的防热瓦,试图靠火箭外部结构+隔热层中间的绝热层“硬扛”热环境,而且这套验证全做完了。
不过要注意,星舰这次飞的不是完整弹道,而是“低热流弹道”——没经历从7.9公里/秒速度下的完整载入过程,也没有长时间烧蚀。所以它作为“实验”是成功的,性能、功能、安全性都验证了,但要成为能商业运营、提供发射服务的运载火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曹梦:航天驭星副总裁/总师
赛博对话:作为研究SpaceX的专家,这次实验的兴奋点是什么?
曹梦:除了彭总说的,绝大多数功能都验证了——比如星舰飞行段的二次点火、星链V3版本模拟卫星的滑动释放机构,最关键的还是刚才提到的“拆防热瓦硬扛热环境”的验证。但必须客观说,它未来要经历的验证还有很多,毕竟没经历完整的高速载入烧蚀。
赛博对话:网友好奇“星舰已经飞了很多次,为什么还在试飞?和猎鹰9的试飞有什么区别?”请曹总科普一下。
曹梦:马斯克早期的运载火箭是小型的猎鹰1号,三连败后第四次发射成功,之后就退役了,转而全力推进猎鹰9。猎鹰9经过不断试飞,从一次性火箭迭代到“一子级重复使用”,现在已经是SpaceX的“常态化发射产品”——前几天猎鹰9的发射次数已经突破400次了,是成熟的商业运载工具。
星舰和猎鹰9的核心区别在“规模”:猎鹰9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20吨,而星舰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能达到近200吨,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传统航天有句话“运载火箭能力有多大,航天舞台就有多大”——未来大规模空间基础设施建设、送更重的载荷去更远的地方,必须靠星舰这种超重型火箭。
赛博对话:SpaceX旗下有火箭和卫星业务,怎么看星舰与Starlink的关系?
曹梦:SpaceX走的是“大系统垂直整合、自研闭环”模式。传统航天里,发射场、火箭、卫星是不同单位负责,协调成本高、难统筹;但SpaceX从发射场到火箭再到卫星,全链条自研闭环,能实现高度定制化。
比如Starlink早期的“一箭60星堆叠式部署”,卫星扁平堆叠、释放方式都是和火箭高度集成的一体化设计,让运载能力最优,实现大规模快速部署。这种“前端产业链一体化设计”,正是垂直整合模式的优势。也难怪有人说SpaceX是“行业百草枯”——它把全链条都做了,其他公司很难竞争。
彭小波:补充一下,SpaceX的设计始终围绕宏大目标:一方面靠Starlink建全球低轨互联网星座,所以卫星设计、火箭快速发射、低成本部署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另一方面,星舰作为超重型火箭(起飞规模5000多吨、推力7000多吨,比土星五号还大),还要支撑“载人上火星”的任务。它的技术路径和应用场景,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赛博对话:马斯克提的“第一性原理”,曹总怎么理解?
曹梦:我理解的“第一性原理”,是他直接瞄准最终目标,不被过程中的细节束缚。比如他的目标不是“造火箭”,而是“上火星”——因为要上火星需要火箭,而当时没有合适的,所以才自己造;如果有现成的,他可能不会花精力自研火箭。
比如他最早想找俄罗斯买战略导弹改火箭,俄罗斯不卖,他才被逼着自己做。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会倒推“怎么实现最优路径”:需要高性能发动机,就自己研;火箭和卫星要匹配,就做一体化设计;分系统要最优,就全链条自研。这种“以终为始”,就是第一性原理的体现。
赛博对话:SpaceX的“快速迭代、以飞带试”模式,和传统航天有什么不同?彭总怎么看这种模式对中国商业航天的适用性?
曹梦:SpaceX的快速迭代,是“不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地面论证”——尽快让火箭达到飞行实验条件,飞完发现问题就改,改完再飞,靠飞行实验迭代。这对传统航天是颠覆,不只是中国,美国传统航天也一样。
比如美国用国家资金搞航天时,研制路径也保守——要对纳税人负责,必须稳妥;但SpaceX是商业公司,能接受试错,追求“快”优先于“一次成功”。
彭小波:中国航天其实也在迭代,从首飞到商业化运营,可靠性、运转能力都在提升,但我们的迭代更偏向“瞄准工程目标设计,围绕目标改进”,追求每一步稳、每一次实验成功;SpaceX则是“试错式迭代”,对失败包容度更高,更强调速度——“允许失败,但要快”。
我们也在进化,但国情对失败的宽容度有限。比如一发火箭成功,需要所有环节、所有人都做对;但失败的原因可能有无数个,试错成本高,所以我们更倾向“走得稳”。
赛博对话:SpaceX的“全自研、垂直整合”,为什么重要?
曹梦:全自研能实现“全流程自主可控”——质量、技术、进度、成本都能自己把控。比如如果发动机靠供应商,迭代时要协调供应商改,周期会很长;但自己研,想改就能快速调整。前期自研是为了快速迭代,等规模化生产后,再逐步引入供应商也不迟。
马斯克做Optimus人形机器人也是如此,核心部件全自研——因为他要的技术路径是自己设计的,外部供应商满足不了,只能自己做。
赛博对话:从中国商业航天的进度来看,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和SpaceX有多大差距?
彭小波:SpaceX2002年成立,2010年左右猎鹰1号首次成功,2015年12月猎鹰9首次回收成功;中国商业航天大多2015年起步,如果我们能在2025-2026年实现类似“重复使用”的关键突破,静态看时间差大概10年。但更关键的是,SpaceX在猎鹰9服役的同时,下一代超重型火箭(超重+星舰)的进展远远领先我们——我们可能快实现它过去的目标了,但它新的进展我们才刚起步,这种差距让人有压力。
曹梦:压力主要来自“发射端卡脖子”——卫星批量研制相对容易,堆规模就能上去;但火箭要是上不去,后续所有环节都没用。中国商业航天现在就是“卡在发射端”,不发射、不进入空间,整个行业就没法推进。
赛博对话:中国商业航天试错成本高、失败宽容度低,这对发展有什么影响?
彭小波:火箭是复杂系统,一发成功需要所有环节、所有协作方都做对;但失败的原因可能出在任何一个细节。我们也想快速迭代,但中国国情对失败的宽容度有限——比如美国能接受“回收失败炸发射场”,但我们更看重发射场安全、设施保护,这种情况下,有些技术路径(比如星舰的“筷子夹回收”)短期内在中国走不通。
我们现在做双曲线三号,计划明年上半年发射,目前在总装总测、地面实验同步推进。因为这次实验规模大、成本高,我们必须把每个环节走稳,避免小差错导致大损失,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赛博对话:星际荣耀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的先驱,有哪些关键里程碑?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彭小波:对星际荣耀来说,几个时间点印象很深:2018年9月5日:亚轨道太空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带载荷;2019年7月10日:“焦点-1”液氧甲烷发动机全系统动力试车成功;2019年7月25日:固体火箭“双曲线一号遥一”成功发射入轨——这是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入轨,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民营公司能发射火箭入轨”的国家(全球能独立发射火箭入轨的国家也就10个左右,民营公司更少);2023年11月2日:3.35米直径的垂直起降验证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成功回收——中国首个全尺寸回收实验成功;2023年12月10日:同一枚火箭再次飞行、回收成功,验证了“重复使用”的技术可行性(虽然飞行高度和入轨要求有差距,但完成了先期技术验证)。
接下来的计划是明年通过“双曲线三号遥一”,实现“入轨+海上回收”——这会是中国商业航天的重要里程碑。
曹梦:彭总他们走的是“探路者”的路,早期经历了很多痛苦,但一旦走通,后面的公司会容易很多。比如他们的垂直起降验证,为国内其他公司提供了宝贵经验。
赛博对话:马斯克的Starlink卫星已经有8000多颗,中国低轨卫星只有百颗左右,差距在哪?
曹梦:美国低轨通信星座发展早,是因为它地面通信基础设施有盲区,需要卫星弥补,所以有市场需求、有资本投入。中国的差距主要在“产业化进度”——我们相关研制单位也做了类似技术验证,效果不错,但在规模化部署、商业落地方面,比美国慢。比如Starlink已经实现“低轨卫星与手机直连”,通信速率不低;我们的技术验证也做了,但还没到大规模产业化的阶段。
赛博对话:6G时代的“空天互联网”,对航天会有什么影响?
曹梦:6G的核心是“天地一体化通信”——未来大家用手机上网,不会在意是连基站还是卫星:人少、广域覆盖的地方用卫星,人多、流量需求大的地方用地面基站补热点。这对航天的影响是“卫星会成为通信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需要大规模部署低轨卫星。
美国现在已经在通过Starlink、SD Space Mobile验证“卫星-手机直连”,很可能在6G时代对我们的5G实现“弯道超车”——我们5G靠地面基站、终端产业领先,但未来“基站上天”(卫星)的时代,要是跟不上,就可能落后。
赛博对话:中国商业航天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彭小波:运载火箭可以理解为“天地物流公司”——把客户的载荷(卫星、物资等)安全、可靠地送到预定轨道,通过收取发射服务费盈利。未来还能拓展“载人航天运输”“地球两点间快速运输”,但目前核心还是“发射服务”。
曹梦:补充一下,火箭不只是“送上去”,还能“运回来”——比如未来太空旅游、太空货运返回,都是商业模式的延伸。但现在最核心的还是“解决发射端瓶颈”,有了稳定的发射能力,才能谈后续的商业拓展。
赛博对话:国内商业航天的投资热度怎么样?
彭小波:热度很高。近几年国家支持硬科技,商业航天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得到政策鼓励。投资机构无论是天使轮、早期还是后期产业资本,都很关注这个赛道。和早期相比,现在大家的疑问从“国家让不让做”变成了“技术怎么突破、产品怎么落地”,更聚焦产业本身了。
赛博对话:SpaceX靠“愿景召唤”凝聚人才,中国商业航天怎么打造团队凝聚力?
曹梦:SpaceX的薪酬在美国航天圈不算高,但很多工程师是“粉丝变员工”——认同“上火星”的愿景,成功后有强烈的自豪感。我也在思考,怎么让团队有这种“热血感”——其实“热爱的传递”很重要,比如我团队里很多应届生是看了我的微博来的,因为认同我对航天的热爱。
彭小波:精神层面的感召很重要。比如NASA能用低于互联网公司的工资吸引优秀人才,就是因为“探索太空”的愿景超越了物质驱动。SpaceX也是如此,靠“把人送上火星、让人类成为跨行星物种”的愿景,凝聚了一批愿意牺牲眼前利益的人。
中国商业航天的团队,既要面对“不如体制内稳定”的现实,又要快速迭代,所以需要“目标一致”——让大家看到“中国商业航天能突破技术、实现自主”,这种成就感能带来凝聚力。
赛博对话:对正在成为工程师的年轻人,两位有什么建议?
曹梦: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热爱是最好的导师”。因为喜欢航天,我愿意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工作,学知识快、成长也快,这是正向反馈。只要真的热爱,就不会觉得辛苦,反而会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
彭小波:曹总说的“热爱”很重要,但我想补充——“数理化是最重要的基础”。任何航天技术问题,最终都要靠自然科学的基础科目支撑,比如高等数学、工程力学、材料科学,这些是“地基”,没有地基,再高的热爱也难以落地。
网址:EP32|对话彭小波 x 曹梦:SpaceX如何颠覆传统航天? https://mxgxt.com/news/view/1860354
相关内容
SpaceX发布全新40美元星链迷你路由器:如何在WiFi覆盖中颠覆传统?逆天而行——从PayPal到SpaceX,埃隆·马斯克的科技帝国之路
【第64期/对话】何小军:让“明星合伙人”颠覆传统营销
曹国伟:颠覆与平衡
NASA宇航员分享太空中SpaceX Starlink卫星的奇特视角
何小军:让“明星合伙人”颠覆传统营销
王菲的婚姻传奇:婆媳情谊如何颠覆传统观念?
2025 直播电商新纪元:虚拟主播+AI 互动如何颠覆传统带货模式?
黑料传送门线路一:揭秘背后的秘密与真相,颠覆你对娱乐圈的认知!
传统就是用来被颠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