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文化|风雪驿馆遇知己 啸台诗酒续风流——苏轼尉氏行记
一
一连数日,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
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三日,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离川赴京,冒着凛冽的严寒,长途跋涉,途经尉氏已是入夜时分。
苏轼触景生情,突然想起阮籍“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时,忽然陷入了沉思。阮籍当年身处魏晋乱世,不愿同流合污,便以醉酒避世、白眼蔑俗,或键户读书、或登山临水。突然骤起拜谒阮步兵旧居之念。于是,他对父亲与弟弟说:“父亲,我对阮公夙怀敬慕,今途径其故居,儿想明日登临啸台,一睹当年阮步兵啸傲青云、蔑视礼教的遗迹,感受那份魏晋名士的旷达与不羁。父亲,您看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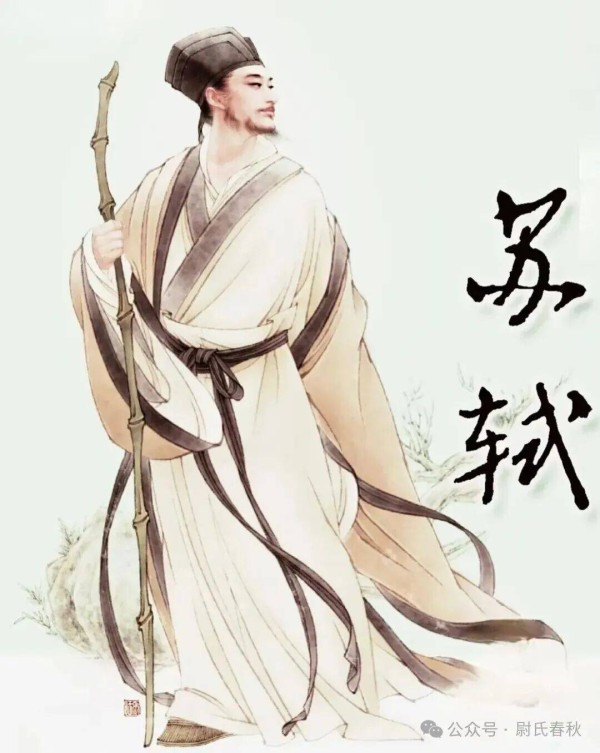
父亲苏洵抖了抖玄狐披风,说道:“今晚,我和子由必须前往京师。”他勒住马缰绳,深情地望着苏轼,眼里闪烁着复杂的情感:“我对阮嗣宗景仰至极,早有瞻谒之意。可宰相韩琦多次来函催促,让我就任秘书省校书郎,无法与儿一同登临啸台,倍感遗憾!”说罢父子相互嘱托几句,挥手告别。

苏轼来到城下,发现两扇朱漆城门早已紧闭。他跳下马,拱手施礼朗声喊道:“守城的兄台,晚生苏轼,自故乡返回京都汴梁,欲往城中拜访好友马石阁、李浮白、张词翰。”
半晌,城楼上探出一个戴着棉毡帽的脑袋,声音裹着寒气飘下来:“先生莫怪,大雪连下数日,县太爷怕夜里有流寇作乱,申时就封了城门,便是州府公差,也得等明日辰时开城。”
监门官向苏轼挥挥手说:“苏先生,我与李浮白交往甚好,久仰您的大名,他常在我面前提起您,说您才高八斗,文采斐然,是当世难得的奇才。我这就去通报您的到来,只是上级有令不敢违抗,城门暂不能开,还望您多多包涵。”监门官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却难掩对苏轼的敬佩之情。
苏轼向监门官拱手道:“承蒙抬爱,多有劳驾!”
监门官闻言连忙躬身回礼道:“苏学士言重了,这是小人分内之事,能为学士效劳,实乃荣幸!”
鹅毛大雪在天地间翩跹起舞,官道上已无往来行人。苏轼抬头望了望渐沉的暮色,正思忖去处,城墙下忽然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先生,城外二里有间驿馆,虽小却也干净,有炭炉热茶,能避风雪。” 苏轼转头一看,是个挑着货郎担的老者。
他谢过老者,调转马头前往驿馆。行至城外,便见道旁有三间茅草屋,门楣上悬挂着褪色的“尉氏驿”牌匾,屋檐下挂着两盏红灯笼,雪光映着灯影,倒有几分暖意。苏轼推门而入,驿卒见他满身是雪,忙接过缰绳说道:“先生快进屋烤火,我这就去给你煮碗姜汤,再烙两张葱花大饼。”
苏轼解下披风,抖落满身雪花,坐在墙角炉火边,望着窗外漫天飞雪,忽然想起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放浪洒脱,不由得心生感慨,此时雪夜受阻之景,倒与阮籍那“车迹所穷”之时有几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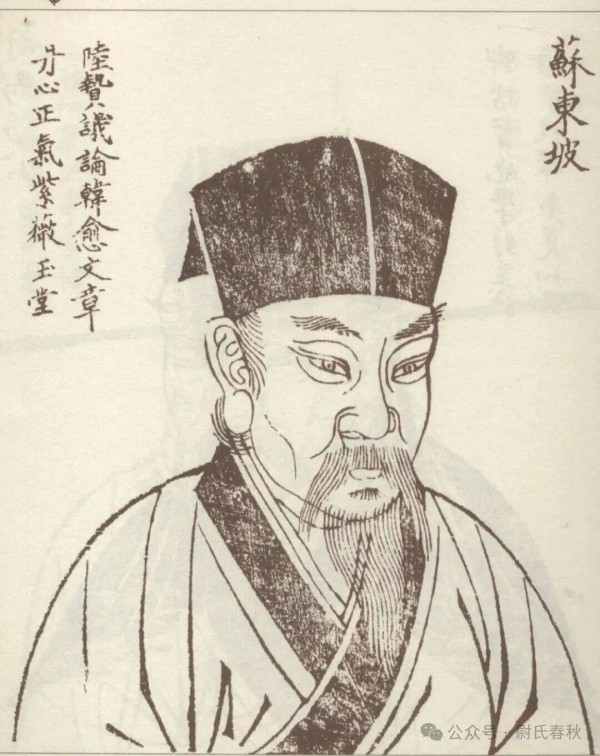
不多时,驿卒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说:“客官请慢用。”苏轼急忙起身接过,连忙答谢道:“承蒙好意,多谢了。”他双手捧碗,小心翼翼地凑近鼻尖,一股浓郁的姜香扑面而来,驱散了些许寒意与疲惫。他随即小啜一口辛辣醇厚的姜汤,望着炉中跳动的火焰,竟觉这驿馆的雪夜,比汴梁的官舍更添几分温馨自在。
忽然,驿站外传来“哒哒”的马蹄声,苏轼抬眼望去,只见那人头戴斗笠,衣衫褴褛,牵着一匹瘦马踉踉跄跄向驿站走来。他浑身是雪、脚步蹒跚,仿佛每一步都诉说着一路走来的艰辛,整个人的状态都透着一股长途跋涉后的倦怠。
驿卒闻声开门,惊呼道:“哎呀,这等风雪之夜,客官从何而来?”来人摘下斗笠,面容黝黑粗糙,两颊泛着冻红,唯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几分坚毅。喘息道:“自北方大漠而来,行程月余,雪大路滑,人困马乏,暂时求个歇脚之处。”
苏轼起身相迎,婉言道:“先生,快来炉边就坐,暖暖身子。”北方客人将马拴在檐下,拂去身上的雪花,趔趔趄趄地走进驿馆。苏轼递上一碗姜汤,问道:“风雪阻途,先生何故孤身至此?”北方客饮了一口姜汤,目光灼灼地说道:“承蒙关照!”向苏轼拱拱手:“我来自北方,欲往江浙一带,途径此地,没想到这雪下得这般凶猛。”
苏轼亲切地招呼他到炭炉边坐下,转身取来两坛美酒,顺手掀开坛盖,递给北方来的陌生客人,顿时,凛冽的酒香瞬间弥漫了整个驿馆。
苏轼说道:“先生,相逢是缘,来一盏驱驱寒气。”边说边缓缓地为自己斟酒。
此时,只见北方客人双手捧起酒坛,快速斟满一盏,仰头一饮而尽。他放下酒盏,脸上泛起红晕,双手抱拳赞赏道:“好酒,烈得痛快。谢谢,谢谢!”他突然话锋一转,感叹道:“人生在世,能有如此美酒相伴,纵然前路风雨飘摇,也当豪情满怀,不负此生啊!”
苏轼执壶的手微微一顿,抬眼凝视北方客人,只见他盏底竟未沾半点酒痕,看得苏轼不由失笑,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与好奇:“豪爽,好酒量,这般饮法,倒是痛快!”他顿了顿,举起酒杯:“寻常饮酒,多是浅斟低酌,细细品味。你这般开怀畅饮,倒是不拖泥带水,不恋栈留痕,当真洒脱。”
“天寒地冻,就得这般烈酒暖身。”客人笑着举起酒坛,又为自己倒满一盏,问道:“先生在此,也是赶路?”
苏轼微微颔首,未主动提及自己的姓名与籍贯,也没有询问客人的尊姓大名。客人见状,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似乎早已猜透几分,也不再刻意追问。只随口谈起北地的风雪、南方的烟雨,以及途中见过的奇人异事。

炉中的炭火渐渐微弱,整个房间的光线也随之暗淡下来。北方客人攥着空盏,脸上带着几分醉意,眼神迷离地望着窗外飘落的大雪,说道:“此地为阮籍故乡,想当年青白眼传世,穷途之哭动情,这般风骨,也许早已融入这里的每一片落叶、每一缕寒风里了。”
苏轼轻声叹:“阮步兵青年时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情壮志,到晚年只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淡然与释然。”
北方客人一遍饮酒,一边感叹:“阮步兵性情放达,蔑视礼教,常将满腹才情与不平付与杯中物。他驾车至穷途而哭,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对世道不公的绝望呐喊,对理想破灭的深深哀恸。”
苏轼慨然道:“世间文墨之士,颇具阮步兵之气概,或有白眼观世之孤介,亦有青眼待士之赤诚。宦海浮沉间,有人俯首任事以担道义,江湖漂泊里,有人佯狂避世以敛锋芒,纵历千年风雨,文士之傲骨,仍在笔墨间含劲未散。”
两人论古今高风、赞贤达亮节、忧社稷之难、诉民间疾苦,不知不觉间窗外已透出熹微晨光。
两人醉意沉沉,苏轼正要问对方姓名,却见那人猛地起身,抓起马鞭,阔步流星迈出门外,飒飒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庭院里显得格外清晰,还带着一股急切与果断。
“先生,这便走了?”苏轼起身,望着匆匆离去的北方客人,眉头微蹙,眼中闪过一丝不解与怅然“敢问先生.....”苏轼欲言又止。
客人翻身上马,回头笑了笑,脸上还带着酒晕:“雪小了些,趁早赶路。”说罢,跃马扬鞭,渐渐消失在朦胧的晨曦中。远处隐隐约约的更鼓声,仿佛在为这突如其来的离别增添了几分萧瑟。
苏轼顿感百无聊赖,望着远去的背影,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袭上心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与不舍,仿佛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随着那背影一同远去,空留他独自伫立在这寂静的驿馆门前。
然而,他与客人的那番畅谈与对饮,还有那洒脱的离别,却化作了雪夜中最难以释怀的永恒。于是,苏轼挥毫写下《大雪独留尉氏》诗一首,以作纪念:
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
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
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
我酌徐徐不满觥,看客倒尽不留湿。
千门昼闭行路绝,相与笑语不知夕。
醉中不复问姓名,上马忽去横短策。
二
雪后放晴,阳光普照,无论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村落,或是鳞次栉比的亭台楼阁都披上了银色的盛装。晴空丽日下的尉氏县城风光如画,显得格外灵秀。
苏轼告别驿卒,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城门口。马石阁、李浮白、张词翰三位挚友早已在此翘首以待,望见苏轼走来,纷纷趋步上前,拱手相迎,眉宇之间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关切与期盼。
马石阁迎上前握住苏轼的手,热情地说道:“子瞻兄,你终于来了!我们盼你很久了。”
苏轼见到昔日的旧友,心中百感交集,不禁忆起嘉祐二年进京应试时,四人同宿一客栈的情景。那时四人围坐灯下,纵论古今兴衰,吟咏诗词歌赋,那份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少年豪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辨。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如今四人境遇各异,或沉浮宦海,或隐逸林泉,然而这份深厚的情谊,却始终未曾改变。
张词翰躬身施礼道:“子瞻兄别来无恙啊!”
张词翰还没有把话说完,李浮白就迫不及待地扑上前,深情地拥抱住苏轼,激动地说:“子瞻兄,春秋三载,弹指一挥间,今日重逢,喜不自胜啊!”
苏轼激动地说:“浮白兄!光阴荏苒,白驹过隙,我们虽然数年未曾谋面,但你我之间肝胆相照之情愈发醇厚,今日重逢,实乃天赐之喜!”
张词翰含笑拱手道:“子瞻兄,久违了!自京都一别至今,小弟心中常感牵挂。今日得以重逢,见兄台精神矍铄、风采依旧,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李浮白亦抚掌大笑:“京都应试,同宿一室,弹指间三载有余,今重逢尉氏,当效魏晋之风抚琴、畅饮、赋诗、论道,再续前缘。”四人相顾而笑,目光在彼此间传递,无需言语便领悟对方所思,他们异口同声:“登啸台!”

四人谈笑风生,迎着朝阳,踏着积雪,穿过街巷,沿着哲湖向啸台走去。

啸台东邻城壕,壕外梅林暗香浮动,沁人心脾;西濒哲湖,湖畔竹海琼枝玉叶,素裹银装。台高约10米,上有一座小庭院,瓦屋三间,厅前花墙围绕,院中有古柏一株,气势挺拔可观。历经数百年风雨,台身虽有些斑驳,却依旧气势不凡。啸台四周的枯树、楼阁、店铺银装素裹,宛如童话世界中的冰雪王国,枝桠间挂满了晶莹的小雪珠,随风轻轻飘落。
四人踏着艳雪覆盖的台阶缓慢而上。
为迎接苏轼的到来,李浮白早已命仆从将庭院中的积雪清扫干净。对大厅进行一番精心布置,铺设毡毯、架起酒炉、摆好茶盏,并特意陈设了一张古琴,静待佳客光临。
苏轼首先登顶,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环顾四周,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激动地说:“雪竹摇曳,红梅点点,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这般清雅绝伦的景致,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啊!”
话音刚落,马石阁已将古琴置于膝上,一曲《鹿鸣》悠然响起,他一边抚琴,一边唱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以此抒发对苏轼的渴慕与欢迎之情,仿佛将满心的敬意与喜悦都融入了这首悠扬、中正、平和的迎宾曲中。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苏轼情不自禁地击掌赞叹道:“多谢石阁兄奏出这等天籁之音,此曲令人回味无穷,既蕴含着高山流水般知音共鸣,又洋溢着主客相得、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真是精妙绝伦啊!”

马石阁笑道:“子瞻兄过誉,不过是借琴声抒怀罢了。”他轻轻抚了一下琴弦,接着说:“想你平日里在案牍劳形之间,难得有这般静心之时,今日有兄台相伴,方能将思念之情化作丝竹之音,也算不辜负这满庭雪景和贤兄的啸台之行。”
此刻,李浮白已将酒炉点燃,醇厚的酒香随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高声吟诵:“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随后,他提壶斟酒,热情地倡议道:“各位贤兄,请移步围炉而坐,我们先共饮三杯,以驱寒暖身!”
说罢,四人举杯相互致意,随即一饮而尽。苏轼放下酒杯,目光投向台下广袤无垠的茫茫雪野,不禁感慨万千:“此台在秦代名为孝母台,相传尉缭曾在此筑台以供母亲纳凉避暑,其一片孝心,足以感天动地。到了魏晋时期,阮公常在此长啸抒怀,故后世又称其为阮籍啸台。今日登临此台,极目远眺,仿佛看到当年竹林七贤傲然独立、洒脱不羁的魏晋遗风。”
张词翰听罢,深有感触地说道:“先生所言极是。此台的历史渊源,实乃中华传统文化中‘孝’与‘志’的生动体现。尉缭之孝,彰显华夏传统美德,为后世树立了孝行典范;阮籍之啸,则寄寓了文人雅士在乱世纷争中坚守气节、追求超然物外的精神魅力。”
马石阁抚弦拨弄,一曲《酒狂》骤然响起,时而悠扬婉转、时而激昂高亢、时而低沉厚重,时而飘逸洒脱。那跌宕起伏的旋律仿佛唤醒了沉睡的魏晋魂魄,将阮籍当年的慷慨长啸化为音符,穿透浩渺无垠的时空,在四位文人的心灵深处激荡回响。
苏轼端起酒杯,向好友拱手示意,朗声道:“今日,赏阮公《酒狂》于啸台之上,更添几分超然物外之情趣。诸位贤兄,何不共饮此杯,以抒胸中豪情与旷达之志?”
四位友人相视而笑,随即举杯畅饮,席间推杯换盏,气氛愈发热烈融洽。他们随着乐曲节奏轻拍案几,那旋律仿佛化为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彼此的心灵紧密相连。在微醺中更添几分旷达与超然。
席间酒香氤氲,乐曲余音袅袅。张词翰提议道:“今登临啸台,拜谒阮公,此情此景此时,若无佳句相和,实乃一大憾事。承望子瞻兄以啸台为题,挥毫赋诗一首,相信定能成就千古佳作,亦让尉氏学子得以沐浴文风,亲聆雅章。”
苏轼说:“久仰词翰兄才情卓著,援笔立成,早已心慕已久,请您先赐一首,以启茅塞,让吾等一睹风采,不知意下如何?”
张词翰闻言,拱手道:“子瞻兄此言折煞鄙人也!兄台乃文坛北斗,词翰区区萤火之光,岂敢班门弄斧?”他轻轻呷了一口酒,缓缓说道:“然今日登临啸台,追慕阮公遗风,又蒙兄台殷殷相邀,若再推辞,恐有不敬。既如此,词翰只得抛砖引玉,以拙句应和之。”言罢,取过笔墨,凝神片刻,随即挥毫泼墨,朗声吟诵:“啸台凌虚接太清,阮公长啸化龙鸣。酒狂一曲穿千古,醉里乾坤任我行。”诵毕,席间诸友击节称赏,举盏相庆,啸台之上酒兴诗情愈发浓厚。
李浮白举杯笑道:“诸位雅兴正浓,倒让在下也技痒难耐,想来凑个热闹。且听我口占两句:啸台相聚共横琴,把酒思古意自深。痛饮千杯君莫笑,挑灯踏雪访竹林。见笑,见笑啦!”
席间诸友皆拊掌赞其豪迈。苏轼举杯应道:“浮白兄此句,酒意淋漓,洒脱自在,可谓是直抒胸臆的佳作啊!”
马石阁亦含笑接话道:“我虽不擅作诗,却可抚琴相和。”说罢,指尖轻拢慢捻,在古琴上缓缓拨动。那琴音时而低回婉转,如山涧清泉流淌;时而高亢激昂,似狂风拂过竹林,在啸台上空久久回荡。
四位雅士沉醉在诗韵与琴声交织的雅致氛围之中,不知不觉中日已过午。在众好友的殷切期盼之下,苏轼提笔挥毫,留下了名篇《阮籍啸台》,以此抒发对阮籍狂达品格、豪迈精神及乱世自保的高度赞赏、深切敬佩与精神共鸣。诗中写道:
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
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
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
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
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
谁能与之较,乱世足自存。
供稿:尉氏县史志学会,来源:尉氏春秋,作者:畅国良
网址:汴梁文化|风雪驿馆遇知己 啸台诗酒续风流——苏轼尉氏行记 https://mxgxt.com/news/view/1828182
相关内容
唐宋文坛对决,李白苏轼谁是“一哥”?请看《长安诗酒汴京花》苏轼和黄庭坚:人生一知己,足以慰风尘
无棣李氏兄弟与苏轼的翰墨缘
苏轼调侃同行好友,写下一首很拗口的怪诗,能一次读顺的都是高手
诗坛知己:苏轼·黄庭坚·米芾
再读《宋史》:原来“古代的偶像”苏轼也有偶像
苏轼和苏子美关系,两人有多倒霉,均因朝中党争遭祸?
苏轼临终一首诗总结自己的一生,英雄末路,满是自嘲,两句很出名
黄庭坚与苏轼之间关系
读城记|超然台上的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