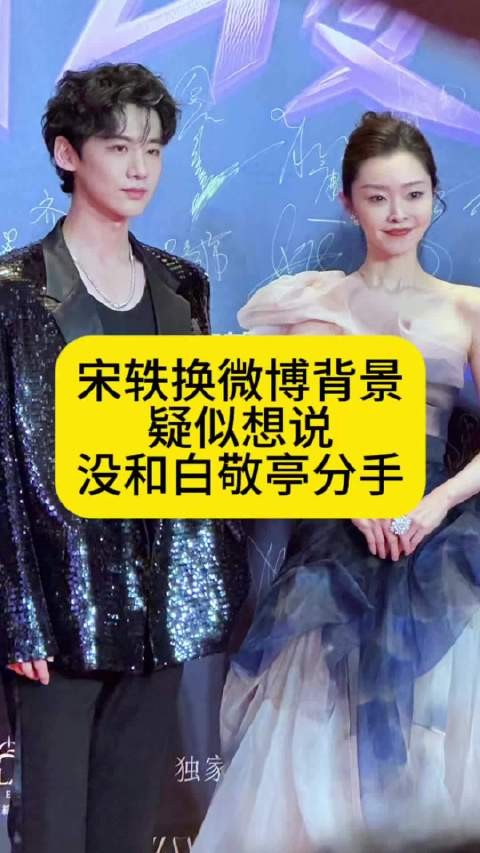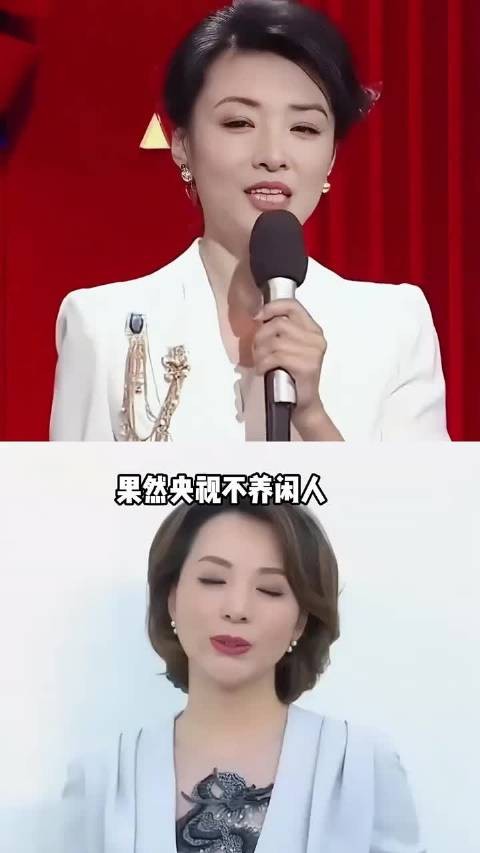三国谈心录:金性尧细说名人轶事
01
千年之前,众多名人在烽火连天的三国时代留下许多为后人传颂的故事。千年之后,这些故事也将成为史学家们竭力考证的史实。一代枭雄曹操的遗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刘备与孙夫人的老少配起因为何?陶渊明为何撰写肉麻的《闲情赋》?甚至,阮籍和嵇康是否有同性之情,仍旧是大家乐此不疲的饭后谈资。
曹操遗书最坦率 内容涉及遗下伎女和衣物处置
曹操的遗嘱,是古今帝王将相当中最人性、最坦率的一篇表白,包括对自己行事风格的省思、丧事的细节安排、后宫婢妾何去何从、子弟如何谋生,等等,尽在其中。由此可见曹操性格里仁厚、体贴、细腻的一面。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曹操卒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年六十六。这篇遗令,不能说是文学作品,但有文人的才情,又值人之将死,上自军国大计,下至后宫生计,款款写来,如见其人,也是他生死之际的最后内心独白。他自己不写,别人是绝对不会考虑到的。历代遗令中,写得这样坦率别致而富于生活感的,曹公之外,即无他人。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神智如此清明,当是逝世之前早就写的,病时服的是“当归”汤,却也不忌讳。
在此之前,曹操已下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西门豹任邺令时,有贤名,民不敢欺。他将其墓选择在西门豹祠附近,大概是这个原因。
当时的伎人,指有技艺的乐户歌女之类,原是良家儿女,与后世的娼妓不同,曹操的正室卞夫人就是倡家出身。又如婢妾,陆机文作婕妤,当是魏国建立后,其内官亦与汉廷相类。下文又说“诸夫人”,曹公内宠之多,于此可见。临终犹殷殷以闺闼为念,生怕她们闲着没事,于是有的守铜雀台,有的织鞋子。刘商《铜雀伎》所谓:“仍令身殁后,尚足平生欲。”
曹公好色而不喜香,内诫令云:“昔天下初定,吾使禁家内不得薰香。后诸女魏(当作‘配’)国家,因此得烧香。吾不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所藏衣,香著身亦不得。”但铜雀诸姬,岂能无香?故有不遂初禁之恨,这一回只得分赠了。说来也真怪,他连香料之微也成为遗令的内容。
02刘备与孙夫人老少配 政治婚姻无疾而终
刘备娶孙权之妹,是一桩各怀鬼胎的政治婚姻。成亲之后,由于互相猜忌,两人并没有住在一起。对孙夫人来说,一个二十来岁的闺女,嫁与四十九岁的刘备,周遭对她多怀敌意,让她有如栖身荆棘。月明星稀,大江东去,举目云天,这心境也是凄凉难堪的,三年多的老少配,终不免要以悲剧收场了。
话说荆州共有八郡,周瑜曾给刘备在江南的四郡,刘备嫌地少不足容众,还想得到江汉间四郡,便于建安二十三年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去见孙权“借荆州”。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所说,江南四郡原为刘备自己所得,不能说是孙吴借给刘备,荆州本为刘表之地,并非吴之故物。
当时周瑜上疏孙权说,刘备是枭雄,要孙权盛筑宫室,多置美女“以娱其耳目”,这便是“美人计”之所本。刘孙联姻,大约即在次年,不过并不是在京口成亲,而是将孙夫人送往荆州。这时刘备四十九岁,孙权二十九岁,孙夫人的年龄不可考,但和刘备相差自在二十岁以上。正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先主传》中所说,孙权以其妹“嫁此近五十之老翁,史文‘进妹固好’四字,大可玩也”。
孙夫人的事迹,在《三国志·蜀书》中提到的共四处,都很简略,只有在《法正传》中,略可见到她的才性: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多到百余人,皆执刀侍立,因而使刘备“衷心常凛凛”。胡三省于《通鉴》引此句下注云:“恐为所图也。”实在已超过“娱其耳目”的范围。
为什么要在《法正传》中记叙她的刚猛?因为法正能够制伏她。刘备在公安时,诸葛亮即感到“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幸有法正辅佐刘备。后来刘备入益州,裴注引《赵云别传》云:“此时孙夫人以权妹骄傲(自恃是孙权之妹而骄傲),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所以刘备事先将赵云留在公安营中以相钳制,足见她确实成为蜀国的威胁。《三国志平话》甚至说周瑜定计,要孙权使其妹暗杀刘备。
孙夫人离刘后的行止,史传即再未涉及,后世却有着离奇的传说。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矶》:“芜湖县西南七里,大江中矶,相传昭烈孙夫人自沉于此,有庙在焉。”
孙夫人的嘉号又有灵泽夫人之称,也因“自沉”而得名,黄仲则有诗云:“空江日落黯祠门,仿佛云裳涕泪痕。一恸无由恩已绝,两家多故事难言。千秋杜宇休啼血,万里苍梧合断魂。终古湘灵有祠庙,流传真伪更难论。”
孙吴联姻,以喜剧形式出现,以悲剧形式结束,联姻并未使蜀吴息争止衅,孙夫人实是政治牺牲品,她与刘备相处大约仅三年,后人对她故亦深为惋惜。
03正名!阮籍嵇康之“异于常交” 并非同性之情
嵇康与阮籍是至交,不仅因为同是竹林的成员,也因两人的才情性行有相似之处,故当时即以嵇阮并称。《世说新语·贤媛》中曾记这样一个故事: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原文为“穿墉”,应是在墙上开个洞,但此事也甚奇怪,似也可解为从墙缝窥视],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韩氏为什么要援引“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的典故,作为自己“意欲窥之”的理由?
晋公子重耳(晋文公)及其随从者狐偃、赵衰在流亡途中,到了曹国,“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骈胁是肋骨相连在一起,这当然是奇征,所以引起曹共公的好奇心。“薄”通“迫”,这里是偷看的意思,因为只有在洗澡露身时才能见到(其实,凭肉眼匆匆偷看,也未必看到骈胁)。
山涛夫人引用这个典故,也是有些缠夹:偷窥骈胁的是曹共公,僖负羁妻看到重耳君臣是在庭堂等地方,她本人并没有偷看过重耳,也不应偷看。她之引用这一典故,大概是说明女人也可自主地去见男人,这且不去计较了。
荷兰学者高罗佩曾著《中国古代房内考》,在第五章中谈到同性恋故事,先引了李白和孟浩然、白居易和元稹,是“这类男性亲密友情的典范”,言下之意,似乎有此嫌疑,“这类友谊是否有同性恋的性质是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是从来无人“争议”过),后来又说“上述四位诗人无一是明显的同性恋”,最后便找到嵇阮身上,还说是“的确有过硬的反证”。过的什么硬?就是《贤媛》篇所记的故事。
下面是高罗佩所要发挥的“过硬”论证:“异于常交”几字已经意味着同性恋关系,但这点是由山涛夫人援引负羁之妻的例子来证实的。她讲的是一个关于晋公子重耳的古老故事。公元前六三六年,重耳及其随从狐偃和赵衰避难曹国。曹公闻其骈胁,想偷看重耳裸体来证实这一点。于是,曹公和一个叫僖负羁的官员以及后者的妻子,在重耳及其随从洗澡的房间的墙上开了一个洞。观后,那位官员的妻子说,这两位随从皆可以相国。显然,她是根据她所窥见的裸体男人的肉体动作而不是他们的谈话才这样讲。因此很明显,山涛夫人选用这个典故是想表明她想验证嵇康和阮籍是否确有暧昧关系。
实在错得太多、太离奇了!
“异于常交”是指山涛和嵇阮二人的情谊,因为这时只有一面之缘,便契若金兰,所以山涛夫人觉得奇怪,所以要试比一下三人的“才致”,而且即使只指嵇、阮二人,也不能武断为“已经意味着同性恋关系”。
观骈胁的只是曹共公一个人,也不是墙上开了一个洞(《左传》只说“薄而观之”),那是山涛夫人的事,作者却说成三个人:共公、僖负羁、僖妻,都在偷看“裸体男人的肉体动作”。洗浴的只是重耳一人,并无狐、赵等随从人员。曹共公只是出于好奇而观骈胁,并无肉体动作之类杂念。
《房内考》作者先确定偷看重耳的“主要”是负羁妻,或者说她也是其中之一,于是又联系到“负羁之妻”云云,以为山涛夫人所窥视的必是嵇、阮的“肉体动作”,这还算什么贤媛?嵇、阮也何至放荡到这个地步?当时两人共眠是很普通的事,山涛就曾与石鉴共宿,还用脚踢过石鉴。
魏晋人重风度、重才识、重器度,因而喜欢品评人物,山涛夫人是贤媛,对丈夫的朋友自很重视。《世说》中每多才致、识度、器量、神气等词汇,这些抽象的概念,用什么样的现代话来表达,实在不容易,但总之山涛夫人要窥视的是嵇、阮的“才致”,看了以后,觉得她丈夫的“才致”不如嵇、阮,所以还是以“识度”相交为宜,山涛即说“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晋书》称山涛有器量,性温雅,这也是抽象的话,但与嵇、阮个性有明显不同,却是事实。
《左传》和《国语》记载观骈胁一事上,行文还不算怎样深奥艰涩,《房内考》作者,先对僖负羁妻的言行作了错误的理解,对山涛夫人也是如此,并以此作为嵇、阮同性恋“过硬的反证”,用中国的成语来说,也就是厚诬古人了。其实,我们只要用常识来想一想,就不会有这样错误的论断,例如在春秋时代,一个大臣的妻子,怎会去偷看客人的洗浴?
04田园诗人陶渊明 竟也写过“肉麻”的《闲情赋》
一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陶渊明,却写了一篇肉麻兮兮的《闲情赋》,他全力刻画一个女子的万种风情,用十个愿望来表达对她的款款深情。归隐山林的陶渊明,为什么笔下如此摇曳生色?
陶渊明是一个高风亮节的田园诗人,诗风也以冲淡著称。他曾经写过《咏荆轲》那种金刚怒目式的诗,后人已多议论。诗之外,又写过几篇赋,也和他的本色符合,可是其中那篇《闲情赋》,后人议论颇为歧异,因为陶集中从无描摹男女恋情的诗,这篇赋却写得很缠绵又很大胆。出于宫体文人,毫不为怪,出于陶公,几乎使人疑心是伪作。
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说:“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后人因此毁誉不一。昭明太子萧统对渊明极为钦重,对此赋却有所指责:“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苏轼却不同意萧说,讥为“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东坡题跋》卷二)。按照苏轼的性格和审美趣味,他之不赞成萧统的批评,原亦意料中事,但萧评是否一无是处,尚待斟酌。
其实,《闲情赋》前有小序:“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陈琳、阮瑀各有《止欲赋》,王粲有《闲邪赋》,寓意都相同,所以陶序说“奕代继作”。
按照陶序的说法,他作赋的动机为了抑制邪心,有助讽谏,也就是警世了。
《闲情赋》的故事是这样的,他遇见一个举世无比、艳色倾城的美女。她的情操淡泊,志趣高尚,却为迟暮易至、人生长苦而悲伤。她揭帷而坐,弹瑟自娱,她从纤指中送出了余音,捋着缤纷的衣袖,露出了皓臂,“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他想主动和她结誓,又恐冒失得罪,他想等凤鸟到来为他通辞,又恐别人已经捷足,因而惶惑不安,神魂颠倒,接下来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柔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一共举了十愿,这里举六愿,这六愿已经接触到她的肉体部分,连她睡的席子、系的鞋带,他都甘心以化身来承当,实在近于亵墨了。
这种手法,陶渊明之前的张衡、蔡邕、王粲也用过,但没有陶渊明那样细致、淋漓而密集。每一愿的下两句,都为自己被遗弃而悲哀,最后是失败了。他的创作动机为了防闲邪欲,这一点我们也可相信。
但是,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有一段很精辟的**:“昭明何尝不识赋题之意?唯识题意,故言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其谓‘卒无讽谏’,正对陶潜自称‘有助讽谏’而发,其引扬雄语,正谓题之意为‘闲情’,而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流宕之词,穷态极妍,澹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不敌摇惑,以此检逸归正,如朽索之驭六马,弥年疾疢而销以一丸也。”这是说得很公道的。
网址:三国谈心录:金性尧细说名人轶事 https://mxgxt.com/news/view/1394078
相关内容
古代“高考”名人的趣闻轶事葡萄酒名人轶事图片大全(葡萄酒名人轶事图片大全集)
陈斐评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古诗评注的向上之路(上)
轶事
宋轶真的当过小三吗 宋轶发浴袍照片给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
神州轶闻录:故都文化趣闻
名人轶事的意思
董新尧:非议与赞誉齐名的现象级视频网红丨网红说
民国轶事(全十册)
娱乐圈421是什么意思 记录了明星的绯闻轶事